夏天最毒的那阵日头过去,秋风就带着刀片子似的凉意,悄没声地卷过来了。田里的庄稼黄了梢,树叶也开始扑簌簌地往下掉,露出光秃秃的、指向灰白天空的枝杈。
日子还是那个过法。我爹的烟袋锅子抽得更凶了,我娘扫院子的笤帚,能把地皮刮下一层来。村里人见了我们,点个头的动作总算自然了些,虽然话还是不多。那道看不见的篱笆,好像被秋风刮薄了一点,但也仅此而已。
我床头那个油布包裹,一直没打开。就放在那儿,挨着枕头,和那个深紫色的旧布袋做伴。有时候夜里睡不着,我会伸手摸摸它们,一个粗砺冰凉,一个隔着油布也能摸出里面衣料的柔软和药材的硬棱。摸完了,心里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,空落落的,又好像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,沉甸甸地往下坠。
他再没出现过。村尾的道观安静得像座真正的荒坟。只有风吹过破木板时,偶尔发出“呜呜”的响动,像是叹息。
我以为,日子就会这么一直沉下去,沉到看不见的底。直到那天。
是个阴天,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,空气又湿又重,闷得人喘不过气。我娘让我去邻村亲戚家送点新打的枣子。回来时,天色已经暗沉沉的了,风也大了些,卷着地上的落叶和沙土,打在脸上生疼。
为了赶在天黑前到家,我抄了近路,还是村后那片老坟岗。心里明明发怵,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快了些,只想赶紧穿过这片地方。
刚走到坟岗中间那条被荒草掩了一半的小路上——
脚步猛地顿住了。
不是看见了什么,是**感觉**到了。
一股极其阴冷、粘腻的气息,毫无预兆地从旁边一座塌了半边的老坟后面,弥漫开来。那气息带着浓重的土腥味,还有一丝……极其熟悉的、冰冷的檀香味。
不是平时飘忽不定的那一丝,而是凝实的、带着恶意的。
我浑身的汗毛瞬间炸起,血液好像一下子冻住了。想跑,腿却像灌了铅,钉在原地。
眼角的余光,瞥见那座老坟后面,荒草无风自动,簌簌地响。紧接着,一个**影子**,慢慢地、贴着地面,“流”了出来。
不是人形,也不是兽形。更像是一滩浓稠的、不断变幻形状的**黑影**,边缘模糊,不断有细小的、触手般的黑气伸出来,又缩回去。黑影的中心,两点针尖大小的、猩红的光芒,幽幽地亮着,正正地“盯”着我。
是它!
那团从他眉心里扯出来的黑雾!它没散!它一直在这里!在这坟岗里!
巨大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,死死扼住了我的喉咙,连惊叫都发不出来。我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滩黑影,贴着地面,无声无息地,朝着我“流”过来,速度不快,却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和冰冷。
完了。
这个念头清晰地砸进脑海。
就在那黑影即将触及我脚面,那两点猩红几乎要贴上我眼睛的瞬间——
我怀里,贴身放着的那个**旧布袋**,和枕头边那个一直没打开的**油布包裹**,同时,**滚烫**了起来!
不是一种烫法。
旧布袋是瞬间爆发的、几乎要烧穿皮肉的灼痛,像上次一样。
而油布包裹里的东西——隔着层层布料,我清晰地感觉到——是那张**黄纸符**!它像是被无形的火焰点燃,爆发出一种灼热的、却带着沉静力量的热流!两种滚烫,一种狂暴,一种沉凝,同时从我胸口和背后传来,狠狠撞进我的身体!
“啊——!”我短促地惨叫一声,痛得弯下腰,差点跪倒在地。
而就在这剧痛袭来的刹那,那滩几乎要贴上我的黑影,像是被滚油泼到的雪,“嗤”地一声,猛地**向后缩去**!边缘炸开一团混乱的黑气,那两点猩红的光芒疯狂闪烁,发出一种无声的、尖锐的嘶鸣!
它怕!怕这烫!怕这符!
这个认知,像一道闪电劈开我混沌的恐惧。求生的本能压过了剧痛,我猛地直起身,根本来不及多想,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那个烫得惊人的旧布袋,又从背后(不知怎么就把油布包裹扯到了身前)隔着油布,死死按住里面那张同样滚烫的符纸!
我把这两样滚烫的东西,胡乱地、用力地,朝着那团缩退的黑影,**一起按了过去**!
没有碰到实体。
但在我的手指(隔着布袋和油布)即将触到那团黑影边缘的瞬间——
“轰!”
一声沉闷的、仿佛来自地底的爆响!
不是声音,是感觉。一股无形的、巨大的冲击力,以我按过去的地方为中心,猛地炸开!
那团黑影发出一声凄厉到极点的、直接响在脑海里的尖啸,整个形体骤然**溃散**!像被狂风吹散的浓烟,瞬间化作无数缕细小的、扭曲的黑气,朝着四面八方激射而去,没入荒草、坟茔、泥土,消失得无影无踪!
那两点猩红的光芒,在溃散的最后一瞬,似乎极度不甘地、怨毒地“瞪”了我一眼,然后彻底熄灭。
阴冷粘腻的气息,潮水般退去。浓烈的檀香味,也瞬间消散。
坟岗里,只剩下呼啸而过的秋风,和荒草被吹倒的沙沙声。
我瘫软在地上,手里还死死攥着那个已经不再滚烫、反而变得**冰冷刺骨**的旧布袋,和那个油布包裹。包裹里的黄纸符,也失去了所有热度,隔着布料,摸上去只是一张普通的、微凉的纸。
冷汗浸透了里衣,被风一吹,冻得我牙齿打颤。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,撞得我耳膜生疼。
我挣扎着爬起来,踉踉跄跄地往回跑,不敢回头看一眼。
一直跑到能看见村里灯火的地方,我才敢停下,靠着路旁一棵老树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低头看向手里。
深紫色的旧布袋,颜色似乎……更淡了一些,像褪了色。系口的麻绳,彻底变成了灰白色,毫无光泽。
油布包裹……我颤抖着手打开。里面的黄纸符,完好无损,但上面原本鲜艳刺目的朱砂符文,此刻颜色黯淡了大半,像是被水洗过,又像是耗尽了所有灵性。
我把符纸紧紧攥在手里,冰冷的纸面贴着滚烫的掌心。
结束了?
“它”……这次是真的……没了?
我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,这两样他留下的东西,在最后关头,救了我的命。也耗尽了它们最后的力量。
回到家,我爹娘看我脸色煞白,魂不守舍,问我怎么了。我摇摇头,说走路绊了一下,吓着了。
他们没再多问。或许是不敢问。
夜里,我把那颜色黯淡的符纸,小心地折好,重新放回油布包裹里,和那套半旧的衣裙、药材、灶糖放在一起。旧布袋我也仔细收好,放在旁边。
它们现在,真的只是普通的物件了。
我躺在床上,睁着眼睛,望着漆黑的屋顶。
眉心那块皮肤,不知何时,又开始隐隐**发烫**。不是灼痛,而是一种温温的、持续的暖意,从骨头里透出来。
我抬手摸了摸,触手平滑,并没有什么异常。
但那暖意,实实在在。
窗外的秋风,一阵紧过一阵,摇着窗棂,发出呜呜的声响。
冬天,真的快要来了。
几天后的一个清晨,霜很重,地上白白的一层。我起得早,去院门口抱柴火。
一打开院门,就愣住了。
门槛外面的泥地上,放着一小捆**码得整整齐齐的干柴**。柴是上好的硬木枝子,劈得粗细均匀,捆扎得结实利落。柴捆旁边,还放着两只肥嘟嘟的、已经断了气的**山鸡**,羽毛鲜艳,用草茎拴着脚。
柴捆和山鸡上,都落了一层薄薄的白霜。
干干净净,没有脚印,没有字条。
像是凭空出现,又像是……早就放在那里,等着霜降。
我蹲下身,摸了摸那柴。木头干燥坚硬,还带着山野清晨的寒气。山鸡的身体已经僵硬,羽毛冰冷。
我抱起柴,拎起鸡,走回院子。柴火放进灶间,山鸡挂在檐下。
我爹起来看见,愣了一下:“这柴……这鸡……哪来的?”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,声音很平静,“放在门口的。”
我爹张了张嘴,看看柴,又看看我,最终什么也没说,拿起斧头,闷头劈柴去了。柴火劈开时,发出清脆的“咔嚓”声,在清冷的晨 air 里传得很远。
我娘看着那两只山鸡,脸上露出这些日子以来,第一个真心的、却又带着复杂神情的笑容:“倒是肥……正好,给你补补身子。”
那天中午,饭桌上难得有了荤腥。山鸡汤熬得奶白,香味飘出老远。
我埋头吃饭,汤很鲜,肉很嫩。热气氤氲上来,模糊了视线。
从那以后,每隔十天半月,总有些东西,会在清晨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家门口。
有时候是一小袋新磨的玉米面,颗粒粗糙,却散发着阳光的味道。有时候是几把鲜嫩的、还带着露水的野菜。有时候是几只野鸟蛋,用柔软的干草小心地垫着。最多的是柴,干透的、耐烧的硬柴,总是码得整整齐齐。
没有一次遇见人。也没有任何标记。
只有东西。
实实在在的,能入口、能烧火、能暖身的东西。
我爹娘从一开始的惊疑,到后来的沉默接受,再到偶尔,我娘看着那些东西,会轻轻叹口气,说一句:“也是个……有心的。”
有心?
我听着,不说话,只是默默地把东西收好,该放的放,该吃的吃。
日子就这样,在柴米油盐、在门口悄然出现的物件里,一天天滑过去。秋风越来越利,刮得人脸生疼。田里的庄稼收完了,场院光秃秃的。天空变得又高又远,是一种冷冷的、透明的蓝。
村尾的道观,依旧沉默。只是听路过的村人说,那观门好像彻底修好了,虽然还是旧木板,但严丝合缝,不再漏风。观前也总是干干净净的,像是有人时常打扫。
我没再靠近过。只是有时站在自家院门口,望着村尾的方向,能看见那小小的、沉默的轮廓,立在冬日苍黄的天幕下。
眉心那点温温的暖意,一直都在。不烫,不冰,只是在那里,像一粒埋在皮肤下的、永远不会发芽、却也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。
腊月二十三,小年。村子里零零星星响起了鞭炮声,空气里飘着糖瓜和炖肉的香气。
那天傍晚,我帮着娘扫完屋子,正在灶前烧火。火光映着脸,暖洋洋的。
院门外,似乎有极轻微的脚步声停下。
很轻,但我听见了。
我的心跳,没来由地漏了一拍。
我没有动,依旧看着灶膛里跳跃的火苗。
过了一会儿,那脚步声又响了起来,不疾不徐,渐渐远去,消失在暮色里。
我娘在里屋喊:“丫头,火别太旺了!”
“哎。”我应了一声,往灶膛里塞了一根硬实的柴。
那柴劈得很规整,烧起来很旺,噼啪作响,火星子溅出来,亮闪闪的。
我盯着那火光,看了很久。
外面,天色彻底黑了下来。远处谁家又放了一挂小鞭,噼里啪啦,炸开一片短暂的热闹,随即归于更深的寂静。
风从门缝钻进来,带着腊月特有的、凛冽的寒意。
灶膛里的火,还在静静地烧着,照亮我半张脸,也把墙上我们俩晃动拉长的影子,模糊地交叠在一起。
屋子里,很暖和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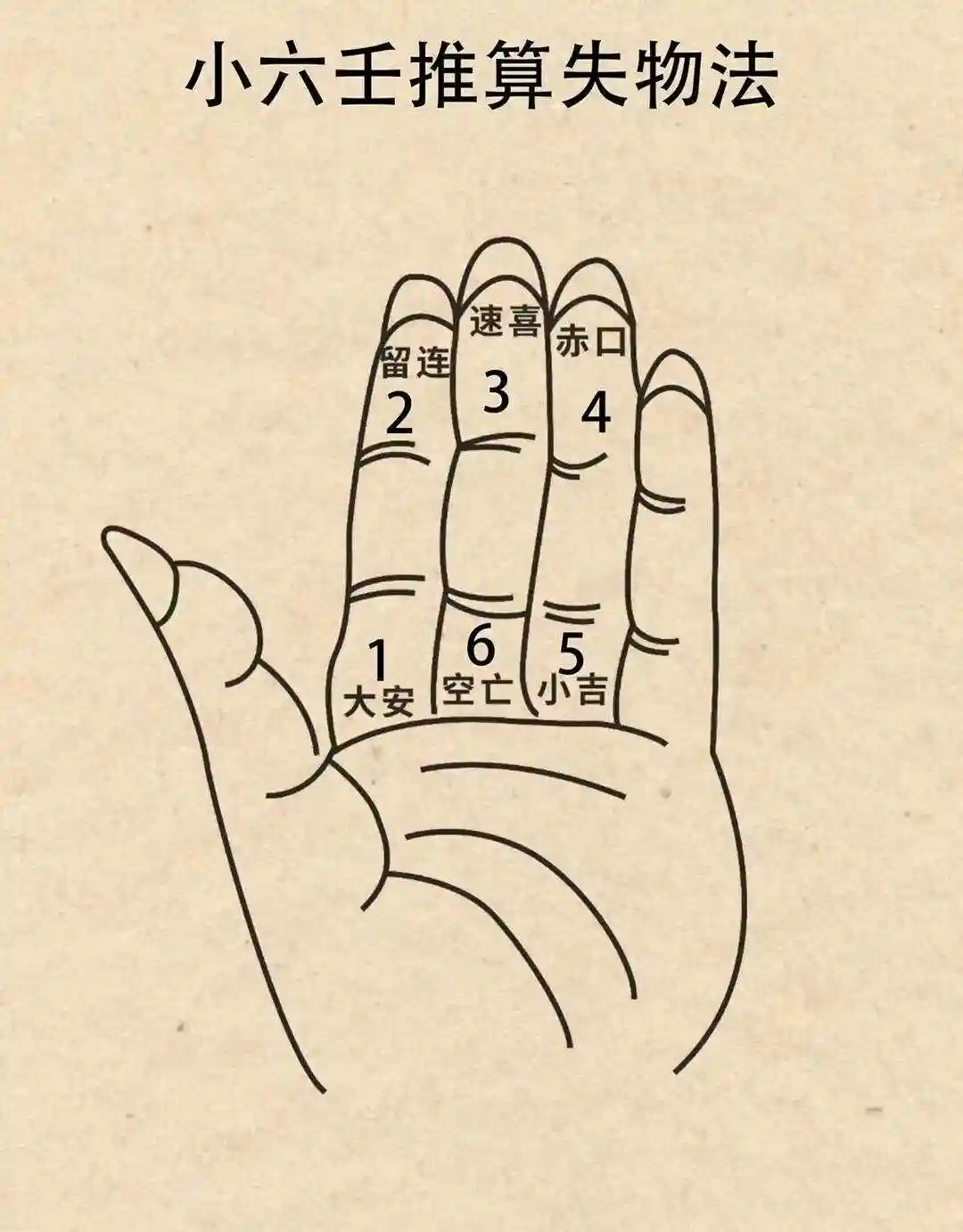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