雪下了又停,停了又下,断断续续的。道观那边再没传来什么骇人的动静,村里人也渐渐把那夜的门响和隐约的传说,当成茶余饭后褪了色的淡资。日子像冻住的河水,表面凝了一层薄冰,底下是看不清的暗流,但总归是往前淌着。
我爹娘脸上的愁苦,被日复一日的劳作磨得平了些,只是偶尔看着我,眼神里还是会闪过一丝复杂的、欲言又止的东西。我装作没看见。
开春化冻的时候,村东头的刘老三家办喜事,娶媳妇。吹吹打打,红绸子挂满了院门,全村老少吃席。我爹娘也去了,带着一份不算厚、但也不失礼数的贺礼。我也跟着,坐在席面角落里,听着一片喧闹,看着那些许久不曾正眼瞧我们家的村人,因为主家的喜气和酒意,偶尔也会朝我们这边举举杯,含糊地说两句“吃好喝好”。
好像那无形的篱笆,松动了一些。
只有我自己知道,有些东西是化不掉的。比如总在夜深人静时飘来的檀香,比如眉心那块皮肤在特定光线下隐隐的异样,还有怀里那个始终冰凉、却再也没烫过的旧布袋。
春耕忙完,天热起来。这天黄昏,我娘在院子里收晒了一天的被褥,忽然“咦”了一声,拎起一件我爹的旧褂子,对着光仔细看。
“这领子后头,什么时候破了这么个口子?”她嘀咕着,“还烧糊了边似的。”
我心里猛地一跳。
那褂子……是那夜从我爹柜子里翻出来,撕了给他包扎腰伤的。
我走过去,接过褂子。领子后面,靠近肩膀的位置,确实有一道寸许长的口子,边缘布料焦黑卷曲,像是被极热的火舌飞快地舔过,又像是……被什么带着灼热腐蚀性的东西溅到。
布料焦黑的痕迹,和他那夜道袍后背撕裂处的焦痕,几乎一模一样。
我拿着褂子,手指摩挲着那处焦痕,粗糙的触感下,仿佛还能感受到那夜观里狂暴的冰冷与滚烫。我娘还在旁边念叨着补补还能穿,我胡乱应了一声,攥着褂子,心里乱糟糟的。
就在那天夜里,我做了个梦。
不是噩梦。梦里没有黑暗,没有鬼影,也没有搏杀。只有一片混沌的、灰白色的雾。雾很浓,什么也看不清,只能听见一种声音,像是风声穿过极狭窄的缝隙,又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,用极其古老的调子,念诵着什么。我听不清字句,只觉得那声音苍凉、平直,一遍又一遍,循环往复。
我就飘在那片雾里,听着那声音,心里异常的平静,甚至有点昏昏欲睡。
忽然,那念诵声停了。
雾气的深处,毫无预兆地,亮起了两点针尖大小的、猩红的光。
冰冷,死寂,带着捕食者的专注。
和我那夜在他眼眶里看到的,一模一样。
我悚然一惊,想逃,身体却动弹不得。那两点猩红的光芒,在雾中缓缓移动,朝着我“看”了过来。
越来越近,越来越近……
就在那红光几乎要贴上我眼睛的瞬间——
“叮铃……”
一声极其清脆、空灵的**铃铛响**,不知从何处传来,像一滴冰水落入滚油,瞬间打破了梦境!
我猛地睁开眼,从床上弹坐起来,浑身冷汗。
屋里黑漆漆的,只有窗纸透进一点朦胧的月光。四下寂静,哪有什么铃铛声?
是梦。只是梦。
可那两点猩红,和最后那声铃响,却清晰得可怕。
我喘着气,手下意识地摸向枕边。空的。那个旧布袋,我向来是贴身放着的。
我掀开薄被,手忙脚乱地在身上摸索,终于在心口处摸到了那个小小的、冰凉的布袋。我把它掏出来,紧紧攥在手里。
布袋依旧是凉的,毫无异常。
可刚才梦里那声铃响……
我再也睡不着了,睁着眼睛,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。
第二天,我神思恍惚,干活总出错。我娘看我脸色不好,摸了摸我的额头,问是不是不舒服。我摇摇头,没说话。
傍晚,我去村口老井打水。井台边没人,只有夕阳把我和井架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我把木桶放下去,听着轱辘转动的声音,脑子里却还是那两点猩红和那声铃响。
水桶沉甸甸地提上来,我俯身去拎。就在我弯下腰,视线掠过幽深井口的那一刹那——
水面倒影里,我的脸旁边,毫无预兆地,**多了一张脸**!
一张戴着斗笠的、模糊的侧脸!斗笠边缘低垂,看不清面容,只有下巴的线条,在荡漾的水波里显得冷硬。
是他!
我骇得手一松,水桶“哐当”一声砸在井沿上,溅起一片水花。我猛地直起身,回头!
井台边空荡荡的,夕阳斜照,只有我的影子,和地上泼洒开的一片水渍。
没有人。
我心脏狂跳,按住胸口,那里,旧布袋贴着皮肤,依旧冰凉。
是眼花?还是……
我定了定神,再看向井里。水面已经恢复了平静,只有我一张惊魂未定的脸。
刚才……是幻觉吗?
我拎起水桶,水洒了一半。往回走的路上,脚步都是虚浮的。
夜里,我又听到了那声音。
不是梦里。是真真切切的,从窗外,从极远极远的地方,顺着夜风,隐隐约约飘进来的。
“叮铃……叮铃……”
很轻,很脆,带着一种奇异的韵律,不急不缓。不是村里货郎的拨浪鼓,也不是谁家檐下的风铃。那声音更空灵,更……古老。
我披衣下床,走到窗边,侧耳细听。
声音似乎是从村尾的方向传来的。
道观?
他在摇铃?
摇给谁听?还是……摇给我听?
我推开窗,夜风带着凉意灌进来,那铃铛声也清晰了些。叮铃……叮铃……一声,又一声,在寂静的春夜里,显得格外突兀,又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寂寥。
我站在窗前,听了很久。直到那铃声渐渐低下去,最终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。
第二天,我没忍住。趁我爹娘下地,我绕到村尾,远远地望着道观。
观门那个豁口,似乎被修补过了,用更整齐些的木板和茅草堵着,不再那么潦草。观前空地上干干净净,连碎砖烂瓦都不见了。整个道观依旧破败,却少了些颓丧的死气,多了点……被打理过的、沉默的生机。
我没看见他。也没听见铃声。
接下来的几天,每到夜深人静时,那铃声总会准时响起。有时候清晰些,有时候模糊些,但总是在那里,叮铃叮铃,不急不缓,像某种固执的呼唤,或者……提醒?
我娘也听见了。有天吃晚饭时,她停下筷子,侧耳听了听,疑惑地说:“这大晚上的,谁家摇铃呢?听着怪疹人的。”
我爹闷头扒饭,瓮声瓮气地说:“管他谁家,睡觉。”
我没吭声。
日子一天天过去,铃声响了大概七八天,忽然停了。
停得毫无征兆。前一天夜里还隐隐约约能听见,第二天就再也没了声响。春夜重新变得寂静,只剩下风声虫鸣。
我反而有些不安起来。那铃声虽然古怪,但至少是个动静。现在连这动静都没了,村尾那座道观,又恢复了往日那种深不见底的沉默。
他……还在里面吗?伤好了吗?那铃……
疑问像藤蔓,在心里疯长。
这天下午,雨下得很大。瓢泼似的,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我坐在堂屋门口,看着雨水在院子里汇成小河,汩汩地流。
忽然,院门外传来一阵不疾不徐的脚步声。
不是村里人那种匆忙避雨的脚步,而是很稳,很从容,一步一步,踏着泥水,由远及近。
我心头一跳,抬眼望去。
雨幕中,一个身影渐渐清晰。
玄青色的道袍,洗得发白,却浆洗得干干净净,穿得整整齐齐。头上戴着斗笠,遮住了大半张脸,只露出线条冷硬的下颌。他手里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,用油布仔细裹着,抱在怀里。
他就这么冒着大雨,走到了我家院门口,停下。
然后,他抬起手,不是敲门,而是将怀里那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,轻轻地、稳稳地,放在了**门槛外面**。
雨水立刻打湿了油布包裹。
放好东西,他后退半步,微微抬起头。
斗笠抬起些许,露出了他的脸。
依旧是苍白的,消瘦的。眉心那个暗红色的疤痕,在雨水的湿气里,显得有些发亮。他的目光,隔着雨幕和院门的距离,准确地落在我脸上。
眼神平静,深得像雨后的潭水,没什么情绪,却也不再有上次窖口对视时那种复杂的审视。只是平静地看过来,像是完成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情。
他看着我,极轻微地,点了点头。
和上次在地窖口时一样,只是下巴往下压了一瞬。
然后,他没再停留,也没等我回应,转身,重新走进滂沱的雨幕里。玄青色的身影很快被雨水模糊,消失在白茫茫的雨帘之后。
我愣在堂屋门口,好半晌,才猛地回过神,冲进雨里,跑到院门口。
门槛外,那个油布包裹静静地躺在泥水里。我弯腰捡起来,包裹不大,有些分量。油布系得很紧,防水做得很好,里面一点没湿。
我抱着包裹跑回堂屋屋檐下,解开系扣。
油布里面,是一块更干净细密的青灰色粗布。掀开粗布——
里面整整齐齐,叠放着一套半新的、**女子的粗布衣裙**。靛蓝色的底子,洗得有些发白,领口袖口绣着极简单的、已经磨损的缠枝花纹。布料厚实,针脚细密,虽然半旧,却浆洗得干干净净,散发着皂角和阳光晒过的、干燥清爽的气息。
衣裙下面,压着一小包用油纸包好的、深褐色的**药材**,我能认出其中几味是补气血常用的。药材旁边,还有几块用干净树叶包着的、黄澄澄的**灶糖**,硬硬的,闻着有股焦香的甜味。
最底下,是一张折成方胜状的、**黄纸符**。
不是上次那种三角符,而是方方正正一张,上面用朱砂画着繁复的、我看不懂的符文,笔画虬结,透着一股沉静的力量。符纸很新,朱砂颜色鲜艳。
我一样样拿出来,摆在干燥的屋檐下,看着。
衣裙,药材,灶糖,符纸。
没有只言片语。
只有门外渐渐小了的雨声,和空气里潮湿的土腥气。
我拿起那张黄纸符,指尖触到微凉的纸面。朱砂的痕迹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极淡的、凛冽的气息,和他身上那种雪后松针的味道很像。
我慢慢地,把符纸重新折好,连同衣裙、药材、灶糖,用青灰粗布仔细包起来,再裹上油布。
然后,我抱着这个还带着室外雨水凉意的包裹,转身走回屋里。
窗外的雨,渐渐停了。云层裂开缝隙,漏下几缕金色的阳光,照在湿漉漉的院子里,泛起一片粼粼的光。
我把油布包裹放在我床头,挨着枕头。
那里,那个深紫色的旧布袋,依旧静静地躺着。
一个是他给的,一个是他送的。
都带着他的痕迹,他的气息,他留下的、看不见也理不清的“因”与“果”。
我坐在床边,望着窗外放晴的天空。
雨后的空气,清新得让人想哭。
远处,村尾的方向,道观的轮廓在澄澈的天光下,清晰又遥远。
他来了。
放下了东西。
又走了。
这一次,连个头都没点。
只有门槛外那滩被雨水冲淡的泥水脚印,证明他真的来过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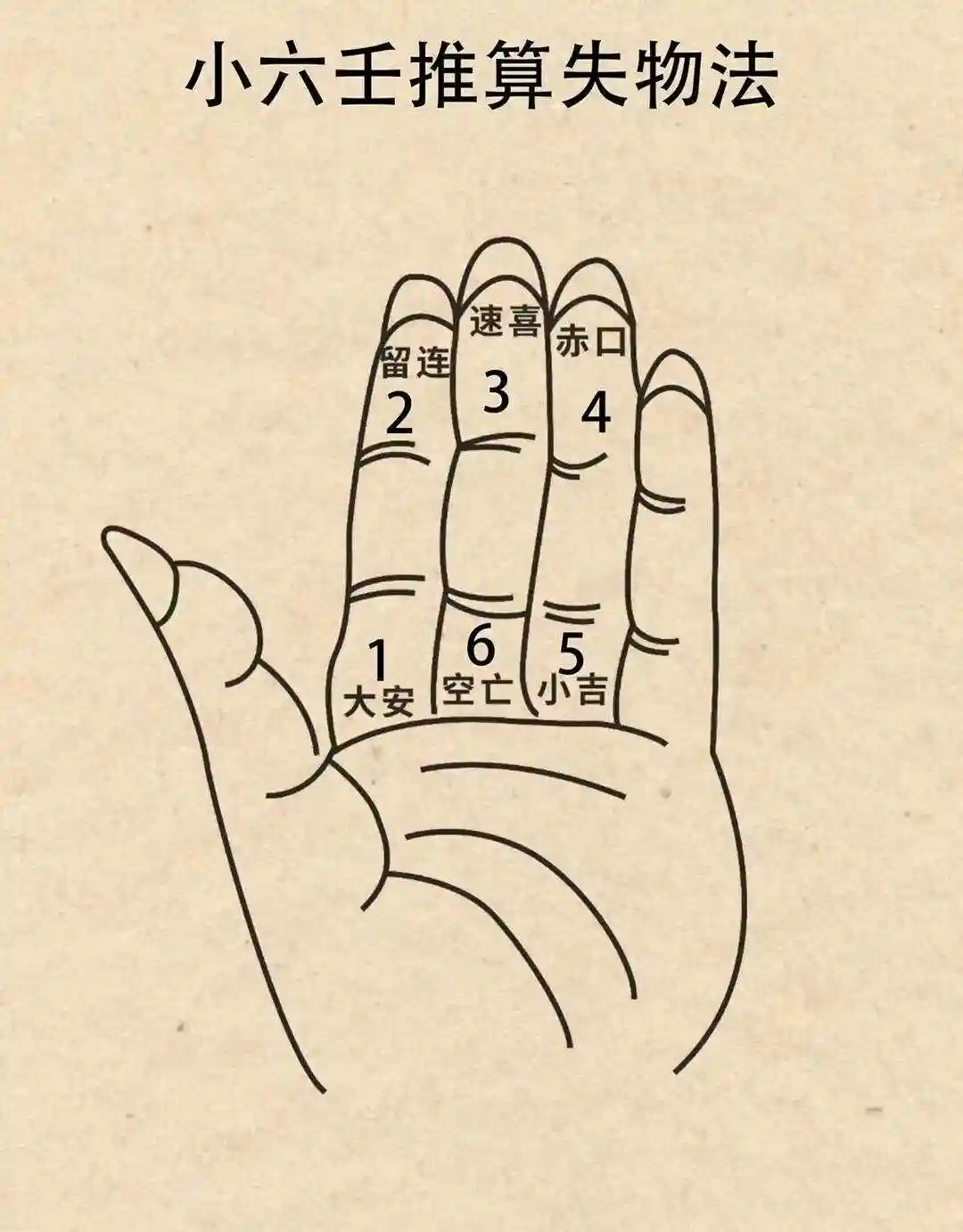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