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再睁开眼的时候,是被阳光刺醒的。
不是清早那种青白的光,是晌午前后才有的、明晃晃、带着热力的日头,斜斜地从破门洞和烂窗纸的窟窿里扎进来,在地上投出几块亮得晃眼的光斑。光斑里,无数细小的尘埃在跳舞,慢悠悠的,懒洋洋的。
我眨了眨眼,适应着那过于明亮的光线。浑身像是被沉重的石碾子细细碾过一遍,骨头缝里都透着酸软和钝痛。左手掌心疼,额头也疼,后脑勺更疼。我试着动了一下脖子,“嘎嘣”一声,僵得厉害。
意识慢慢回笼。昨夜——或者说凌晨——那混乱惊悚的一切,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破碎贝壳,硌得人心里发慌。我猛地扭头,看向旁边。
他还在。
就躺在我旁边不远处那三个叠起来的旧蒲团上,身上盖着我那件脏得看不出原色的外衣。晨光同样落在他脸上,照亮了他比昨夜看起来更加清晰的轮廓。脸色依旧苍白,但不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青灰,而是有了点属于病人的、虚弱的白。眉心那个伤口已经彻底凝结了,暗红色的血痂覆盖着,边缘微微红肿,看着依然吓人,但至少不再流血了。他的呼吸很轻,胸膛几乎看不出起伏,但绵长而均匀,比昨夜那若有若无的样子,实在了太多。
他还在昏睡,或者说,是在一种深沉的、修复自身的睡眠里。眉头舒展了些,眼睫安静地覆着,嘴唇依旧没什么血色,干得起了皮,但不再紧抿着,显得放松了些。
活着。
这个认知,像一块温热的水浸过的布巾,轻轻敷在了我紧绷了一夜、又冷又硬的心口上,带来一点迟来的、虚脱般的慰藉。
我慢慢坐直身子,靠在冰冷的墙壁上。阳光暖洋洋地照在我半边身子上,驱散了浸透骨髓的寒意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,一身衣服又脏又破,沾满了干涸发黑的血迹、灰土和香灰,像刚从泥坑里捞出来。左手掌心的烫伤已经起了厚厚的水泡,有些破了,渗着淡黄色的液体,周围红肿一片。额头肯定也撞破了,摸上去火辣辣地疼。
又渴,又饿,嗓子眼干得冒烟。
我舔了舔同样干裂的嘴唇,目光在观里逡巡。墙角那个被撞瘪了一块的陶罐还在,昨晚混乱中居然没碎。我撑着墙壁站起来,腿脚还是软的,走过去拿起陶罐,里面居然还有小半罐清水,大概是之前残留的,没被香灰污染。
我也顾不上脏,捧起陶罐,凑到嘴边,小口小口地喝了几口。冰凉的清水滑过干涸的喉咙,带来一阵刺痛,随即是难以言喻的舒畅。
喝完了水,我靠着墙歇了会儿,攒了点力气,才重新走到他身边蹲下。看着他干裂的嘴唇,我犹豫了一下,还是捧起陶罐,用手指蘸了点儿清水,小心翼翼地涂抹在他的唇上。清水很快被吸收,他的嘴唇润泽了一点点。
我又看了看他腰间包扎的地方,我爹那件旧褂子撕成的布条已经被血和药粉浸透,变成了硬邦邦的深褐色一团。暂时不能动,一动肯定扯到伤口。
做完这些,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。阳光越来越亮,观里的温度也升了起来,灰尘在光柱里浮沉。外面村子里的声音清晰地传来,鸡鸣狗吠,孩童嬉闹,妇人吆喝,还有货郎摇着拨浪鼓、拖着长腔的叫卖声。一切都恢复了平常,热闹,鲜活,仿佛昨夜那场发生在村尾的、无声的生死搏杀,只是我一个人的噩梦。
只有观里这片狼藉,和躺在这里的我们,是那场噩梦留下的、抹不掉的证据。
我重新坐回他旁边的蒲团上,抱着膝盖,下巴搁在膝盖上,眼睛望着门外那片被阳光照得亮堂堂的空地,耳朵听着外面喧嚣的人间烟火,心里却空落落的,像是破了一个大洞,呼呼地往里灌着冷风。
时间一点点流走。日头从东边慢慢挪到了头顶偏西。肚子饿得咕咕叫,但我一点也不想动,也不想回去。回去怎么说?说我昨夜又跑到道观,还弄成这副鬼样子?
就在我盯着门外一块光斑出神的时候,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极其轻微、几乎听不见的抽气声。
我浑身一僵,猛地回过头。
他醒了。
不是完全清醒,眼睫颤动着,似乎想睁开,试了几次,才勉强掀开一条缝隙。目光浑浊,没有焦距,涣散地望着上方黑黢黢的房梁。嘴唇微微翕动,发出一点含混的气音。
我屏住呼吸,凑近了些,耳朵几乎贴到他唇边。
“……水……”
还是这个字,嘶哑得像是用砂纸磨过。
我连忙端起旁边的陶罐,小心地托起他的后颈,把罐口凑到他唇边。他配合地微微张嘴,我就着罐口,一点点把水喂进去。他吞咽得很慢,很艰难,喉结滚动,发出轻微的“咕咚”声。小半罐水,喂了许久才喝完。
喂完了水,他像是耗尽了力气,眼睛又闭上了,眉头因为不适而微微蹙起。
我把他轻轻放回蒲团上,看着他依旧苍白虚弱的脸,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感觉,似乎被什么东西填上了一点点,虽然还是虚浮,但至少有了着落。
他没死。还能喝水。
这就好。
我在他旁边重新坐下,这次离得更近了些。阳光暖融融地照着我们,空气里的浮尘缓慢地升降。外面的喧嚣似乎也远了些,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。
不知过了多久,可能只是一会儿,也可能很久,就在我以为他又昏睡过去的时候,他又开了口。眼睛依旧闭着,声音比刚才清晰了一点点,却依旧低弱,带着浓重的疲惫。
“……什么时辰了?”
我望了望门外偏西的日头,不确定地说:“怕是……过午了。”
他“嗯”了一声,没再说话。呼吸似乎又平稳了些。
又过了一会儿,他眼睫再次颤动,这次,缓缓地、彻底地睁开了。
目光先是涣散,慢慢聚焦,落在了我的脸上。
那眼神很深,很静,像两潭刚刚经历过暴风雨、此刻水面初平、却依旧幽深不见底的古井。里面没有了昨夜那种空茫的死寂,也没有了痛苦挣扎的暴烈,只剩下一种近乎虚无的平静,和深不见底的疲惫。他看着我的脸,看了很久,目光扫过我额头上已经结痂的伤口,扫过我红肿的左手,扫过我一身狼藉,最后,又落回我的眼睛。
他没有问“你怎么在这里”,也没有问“发生了什么”,只是那么静静地看着。
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,垂下眼,盯着地面上的光斑。
“你……”我犹豫着开口,声音干涩,“你的伤……”
“死不了。”他打断了我的话,语气平淡,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。说完,他又合上了眼睛,仿佛刚才那片刻的清醒,已经用掉了他积攒的所有力气。
观里又安静下来。
阳光继续移动,把我们笼罩在温暖的光晕里。外面村子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,大约是到了午后歇晌的时候。
我靠坐在他旁边的蒲团上,背靠着冰冷的墙壁,眼皮又开始发沉。极度的疲惫和放松后的空虚感,潮水般涌上来。
就在我意识又要模糊的时候,我听见他极轻、极低地说了一句:
“……多谢。”
两个字,轻得像羽毛落地,混在午后暖洋洋的阳光和浮尘里,几乎听不见。
我猛地睁开眼,看向他。
他依旧闭着眼,眉头舒展,像是又陷入了昏睡,只有胸口规律地微微起伏。
仿佛刚才那句话,只是我的错觉。
我怔怔地看着他苍白的侧脸,看着阳光在他脸上投下的、长长的睫毛阴影。
然后,我慢慢地,重新靠回墙上,闭上了眼睛。
这一次,我没有再被噩梦惊醒。
我是被傍晚的凉风吹醒的。
睁开眼,发现身上的阳光已经移开了,只剩下一点金红色的余晖,从西边的窗洞斜斜射进来,在对面墙上涂了一小块温暖的亮色。观里的温度降了下来,带着入夜的寒意。
我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,看向旁边。
他已经醒了,正半靠在垫高的蒲团上,后背倚着墙壁。眼睛望着对面墙上那块金红色的光斑,目光依旧是那种深潭般的平静,只是脸色在夕照下,似乎有了一点点极淡的血色。
听到我起身的动静,他转过头,看向我。
“醒了?”他问,声音比午后时清亮了些,虽然依旧虚弱。
我点点头,嗓子干得不想说话。
他也没再说什么,目光又转回去,望着那点即将消失的夕照。
我站起来,腿脚还是有些发软,但比之前好多了。我走到墙角,拿起那个空了的陶罐,想看看还有没有水。罐底只剩下一点点水渍。
“外面……井边……”他忽然开口,声音很轻,“应该有水桶。”
我愣了一下,看向他。他依旧望着那点夕照,侧脸在渐暗的光线里,显得格外清瘦冷硬。
我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迟疑了一下,我还是拿着陶罐,走出了那个破损的门洞。
外面天光将尽,西边天空只剩下一抹暗红的霞。晚风带着凉意吹过,道观前的空地上干干净净,只有几片落叶。昨夜那些恐怖的痕迹、撞碎的门板,在白天看来,也只是一片狼藉的废墟,少了几分阴森,多了点荒凉。
我走到观旁那口老井边,井绳上果然挂着一个半旧的木桶。我打起半桶清澈冰凉的井水,先自己捧起喝了几口,又仔细把陶罐里外冲洗干净,才装了半罐清水,提了回去。
把水罐放在他身边,我又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。
他伸手,自己拿起了陶罐,喝了几口水。动作虽然慢,却很稳。
喝完了水,他把陶罐放下,目光终于从那点已经完全消失的夕照上移开,落在我身上。上下打量了一番,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。
“……回去。”他说,语气没什么波澜,“你家里……该急了。”
我一怔,心里那股空落落的感觉又回来了。是啊,我出来一天一夜了,爹娘……
“那你……”我看着他腰间的伤,看着这破败漏风的道观。
“我没事。”他淡淡道,“习惯了。”
习惯了?习惯什么?习惯受伤?习惯一个人躺在这破地方?
我还想说什么,他却已经重新闭上了眼睛,摆出了送客的姿态。
我站在原地,看着他又恢复成那副疏离的、石刻般的模样,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闷得慌。昨夜那些生死相依、滚烫冰冷的接触,那最后一声轻不可闻的“多谢”,难道都是假的?都是我的错觉?
站了半晌,我终于还是转过身,慢慢地,走出了道观。
走到门口,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
他依旧半靠在蒲团上,闭着眼,脸隐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,看不清表情。只有那身洗得发白、沾着血污的道袍,在昏暗的光线下,勾勒出一个孤独而倔强的轮廓。
我咬了咬嘴唇,转身,踏着暮色,朝着村子灯火渐起的方向走去。
走出很远,再回头时,道观已经彻底融入了沉沉的夜色里,只剩下一个黑魆魆的、沉默的影子。
夜风很凉,吹在我单薄破旧的衣衫上。
我摸了摸怀里,那个旧布袋还在,依旧冰凉。
眉心被他额头抵过的地方,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湿冷的、血痂的触感。
我加快脚步,朝着家里那点微弱的灯火走去。
身后,是越来越浓的夜,和那座孤零零的、沉默的道观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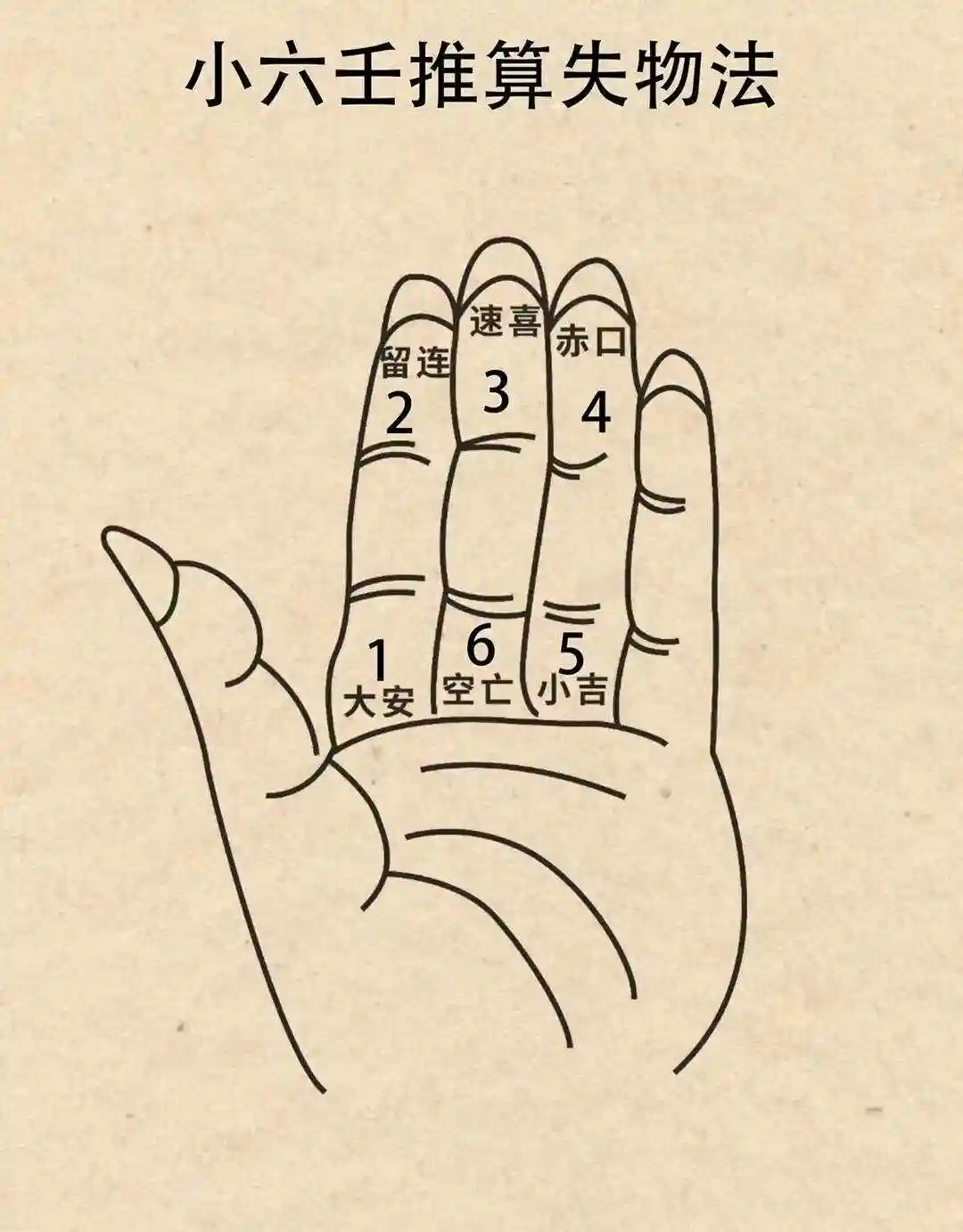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