观里真静啊。
刚才那山崩地裂般的轰鸣、嘶吼、搏杀,全都潮水般退去,一丝痕迹都没留下。连角落里那些不甘心的窸窣鬼影,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抹掉了,干干净净。只有夜风从破损的门洞窗洞灌进来,在空旷的破屋子里打着旋儿,发出单调的、呜呜的轻响,反倒衬得四下里更加死寂。
我额头还抵着他眉心的伤口。温热的血已经不再往外涌了,凝结成一片黏腻发硬的痂,把我们两个的皮肤紧紧粘在一起,分不清是他的血,还是我额头上蹭破皮渗出的血。隔着一层薄薄的、冰冷的血痂,我能感觉到他皮肤下极其微弱的搏动,一下,又一下,像即将熄灭的烛火最后那点不甘心的颤抖。
我睁开眼,视线从一片混沌的血红里慢慢聚焦。先看到他近在咫尺的脸。脸上糊满了血污、汗水和尘土,惨白得没有一丝人色,眼窝深陷,颧骨突出,嘴唇干裂起皮,泛着青灰。只有那双眼睛是睁开的,半阖着,没什么焦距地望着我身后上方某处虚空,里面空茫茫的,像是耗尽了所有,连痛苦都显得麻木。
但人,总归是“醒”着的样子。
我试着动了一下。
脖子僵硬得像生了锈的铰链,发出“嘎嘣”一声轻响。额头上那层血痂被扯动,传来一阵刺痛。我下意识地想往后缩,和他分开。
可我忘了,我们的手还握在一起。
是他先松开的。
就在我动的那一刹那,他那只一直紧紧攥着我的、冰冷而有力的手,五指一松,毫无预兆地,滑落了下去,“啪”地一声轻响,掉在他自己身侧冰冷的砖地上,手指微微蜷曲着,再也没了动静。
紧跟着,他半阖着的眼睛,也缓缓地、彻底地合拢了。眼皮沉重地覆盖下来,遮住了那双空茫的眸子。脸上最后那点强撑着的活气,也像被风吹熄的灯苗,“噗”地一下,灭了。
他又“昏”了过去。或者说,是失去了最后一点维持清醒的力气,彻底坠入了无边的黑暗。
额头上没了那股对抗的力量,我往后一仰,跌坐在地上,带起一小蓬灰尘。后脑勺重重磕在翻倒的供桌棱角上,眼前金星乱冒,疼得我龇牙咧嘴。
但我顾不上疼。
我喘着粗气,看着他又变回那副无知无觉、只剩胸口微弱起伏的样子,看着他眉心上那个被我撞得又渗出一点新鲜血珠的狰狞伤口,又看看自己摊开的、空落落的手掌——刚才被他攥过的地方,还残留着冰冷的触感和一点浅浅的、发白的指印。
刚才……那短暂的、艰难的回握,那渡过来的一丝清明暖流,还有那最后空茫的对视……是真的吗?
还是我疼糊涂了,出现的幻觉?
观里一片狼藉,像被几十头野牛碾过。碎裂的木头,倾倒的香炉,翻倒的神像,满地厚厚的香灰和尘土,还有那一道道刻在地上的、触目惊心的深痕。空气里还残留着极淡的焦糊味和檀香味,混在灰尘的气息里,呛得人想咳嗽。
而我和他,就瘫坐、躺倒在这片狼藉的正中央,身上脸上没一块干净地方,狼狈得像两条刚从泥潭里捞出来的、半死不活的鱼。
外头,天色似乎……亮了一点点?
不是阳光,而是那种黎明前最深沉的黑暗即将过去时,天空泛起的一点点青灰色,极其微弱,却固执地透过破损的窗洞和门洞,挤进观里,勉强勾勒出物体的轮廓。
天,快亮了。
这个认知像一滴冰水,落在我被疼痛和混乱烧灼的脑子里,带来一丝微弱的清明。
不能就这么待着。
这破观四面漏风,阴冷得像个冰窖。他伤成那样,血流了那么多,又昏迷不醒,躺在这冰冷的地上,不用等“那些东西”再来,光是冻,就能要了他的命。
我咬咬牙,撑着地面,想站起来。腿软得像面条,试了两次才成功。摇摇晃晃地走到他身边,低头看着他。
怎么弄?拖?背?我哪有那么大力气?
目光扫过观里,落在墙角那堆破旧的、沾满灰尘的蒲团上。有几个还算完整。我走过去,挑了三个看起来最厚实、也最不破的,抱回来,垫在他身下,尤其是后背和腰腹的位置。又脱下自己身上那件同样脏污不堪、但好歹是棉布的外衣,胡乱盖在他身上。
做完这些,我已经累得眼前发黑,靠着墙滑坐下去,离他不远不近。看着他躺在蒲团上,盖着我的衣服,眉心伤口已经不再流血,只是脸色依旧白得吓人,呼吸微弱但平稳,像是睡着了,只是睡得极沉,极不安稳。
我也累极了,浑身骨头像是散了架,每一寸肌肉都在酸痛。左手掌心的烫伤火烧火燎地疼,额头撞破的地方也一跳一跳地胀痛。我靠着冰冷的墙壁,闭上眼睛。
可我睡不着。
一闭上眼,刚才那混乱狂暴的画面就又涌上来——猩红的眼,搏动的黑雾,冰冷与滚烫交织的洪流,还有他最后那空茫的眼神……
还有他说的,“因果太重,你承不起。”
我猛地又睁开眼,望着观顶黑黢黢的、结满蛛网的房梁。
承不起?
我已经沾了他的血,碰了他的“炁”,额头抵过他眉心的伤口,手被他死死攥过……甚至,还把那团要命的黑雾,用这种近乎同归于尽的方式,给弄“散”了。
这因果,早就缠成一团乱麻,把我死死裹在里头了。哪里还分得清谁欠谁,谁承得起,谁承不起?
外头的天光,又亮了一点点。青灰色变成了鱼肚白,观里的物件轮廓更清晰了些。风好像也停了,只剩下绝对的寂静。
我侧过头,看向他。
晨光吝啬地落在他脸上,照亮他惨白的皮肤,干裂的嘴唇,和眉心那处已经结痂、但仍显得狰狞的伤口。他睡得并不安稳,眉头即使在昏迷中,也微微蹙着,嘴唇偶尔会极轻微地动一下,像是在呓语,却听不清内容。
我看了很久。
然后,极其缓慢地,挪动身子,靠他更近了一些。没有挨着,只是缩在他旁边的蒲团上,背靠着同样冰冷的墙壁。
离得近了,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混合了血腥、尘土、药味和他本身那种凛冽气息的味道,不太好闻,却莫名地……让我那颗一直悬在嗓子眼、咚咚乱跳的心,往下落了一点点。
我抱着膝盖,把下巴搁在膝盖上,眼睛望着那扇破损的、透进越来越多天光的门洞。
外面,村子里隐约传来了第一声鸡鸣。
“喔——喔喔——”
声音遥远,模糊,却像一根针,刺破了这死寂的黎明。
紧接着,更多的鸡鸣声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,远远近近。狗也叫了,还有谁家开门泼水的声音,“哗啦”一下。
人间,苏醒了。
我听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声音,眼皮越来越沉,越来越重。
最后,在越来越亮的晨光和渐渐喧闹起来的、属于人间的声响里,我头一歪,靠在了冰冷的墙壁上,终于支撑不住,昏睡了过去。
失去意识的前一瞬,我模糊地想:
天亮了。
我们……好像都还活着。
只是这以后,这缠死的因果,这眉心留下的疤,还有这空荡荡、冷冰冰的破观……
又该怎么算呢?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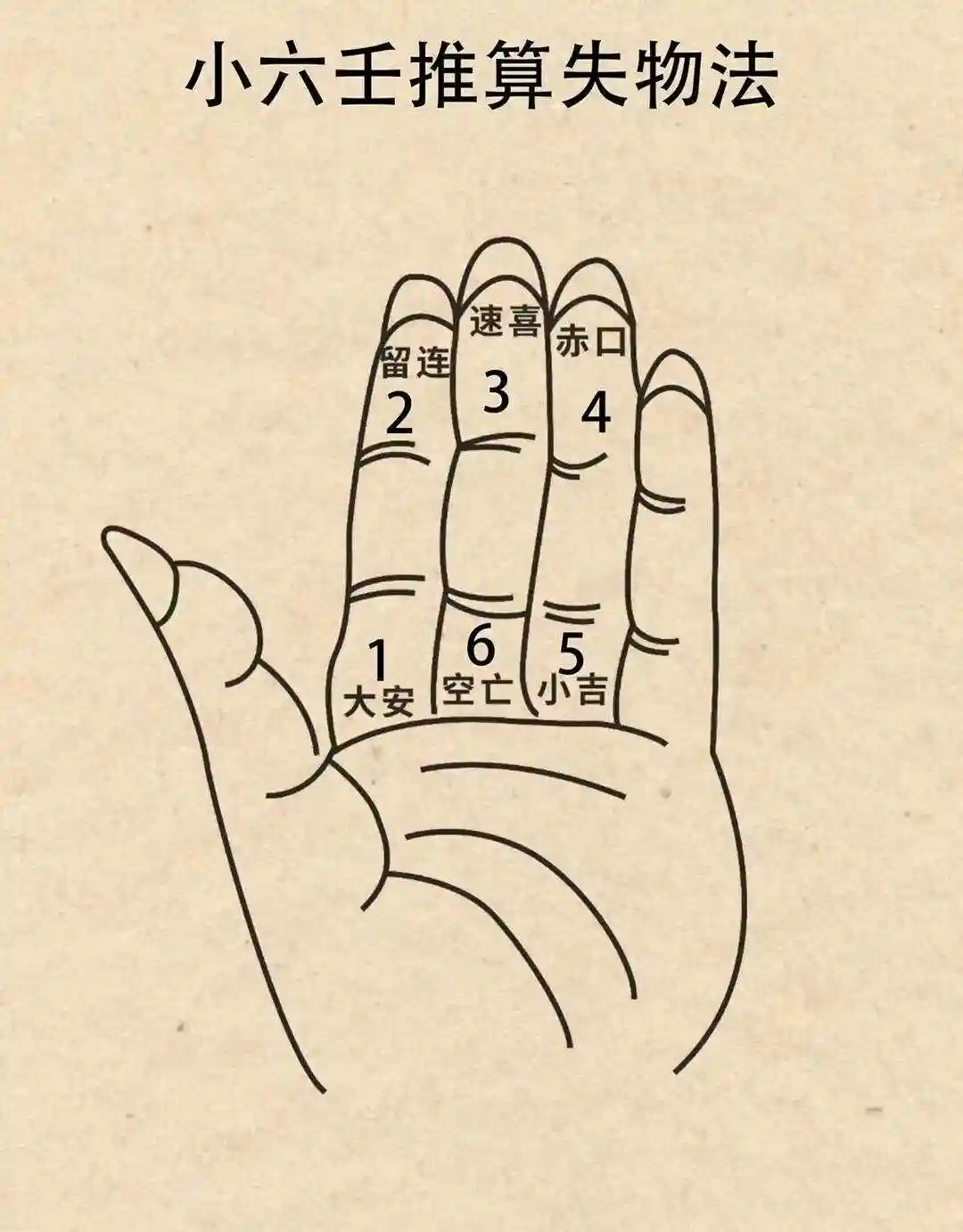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