院子里的落叶又积了一层,黄黄绿绿地铺着,踩上去沙沙响。我娘拿着大笤帚,“哗啦哗啦”地扫,声音闷闷的,一下,又一下,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彻底扫出去。
我爹蹲在门槛上,手里的烟袋锅子就没熄过,青白色的烟雾一团团升起来,散在清冷的空气里。他眼睛盯着地上某块砖,半天不挪一下,脸上的皱纹比前些日子又深了些,像刀刻的。
他们都没问我那天夜里去了哪儿,怎么回来的,又怎么弄成那副样子。我爹第二天早上看见我时,嘴唇哆嗦了几下,最后只重重叹了口气,背着手出了门。我娘给我端来热水和干净的旧衣裳时,眼睛红红的,手有些抖,但什么也没说,只是摸了摸我额头已经结痂的伤,又看了看我缠着布条、依旧红肿的左手掌心,叹了口气,转身去灶间了。
日子就这么过下去。吃饭,睡觉,干活。和以前一样,又处处不一样。
村里人对我们家的态度,像是被冻住了。路上遇见,点点头,含糊地招呼一声,就匆匆走开。没人再来串门,也没人再在背后指指点点——至少不当着我们的面。我们家院子外面那圈看不见的篱笆,好像更结实了。
只有我自己知道,有些东西,是扫不掉,也冻不住的。
我还是怕黑。油灯必须点到眼皮子实在撑不住才吹。夜里一点风吹草动,就能让我惊醒,瞪着黑黢黢的房梁,直到心跳平复。那股清冷的檀香味,时不时还会飘来,有时在傍晚打水时,有时在半夜惊醒的枕边。不浓,却像一根冰冷的丝线,总在不经意间勒我一下。
身体倒是慢慢养了回来,不再那么容易累,手脚也不再总是冰凉。胃口好了些,脸上也有了点血色。额头上和掌心的伤,结了痂,慢慢脱落,留下两块淡粉色的新肉,摸上去有点木木的。
只有眉心那里。
我每天洗脸,都会对着水盆里的倒影仔细看。有时候,那点隐隐的青色好像没了,皮肤平滑如常。可有时候,尤其在傍晚光线昏暗时,或者我心里发慌的时候,又觉得那块皮肤底下,似乎真的透着一丝极淡的、洗不掉的青气,不仔细看看不出来,但自己总能感觉到那里有些异样,温度似乎也比旁边低一点点。
我去过村尾两次。都没走近,只是远远地,站在能看到道观轮廓的地方,望上一阵。
第一次去,是回来后第三天下午。观门那个黑黢黢的豁口还在,用几块破木板潦草地挡着,歪歪斜斜。观前空地上那些碎木烂砖似乎被清理过一些,堆在角落里。整个道观静悄悄的,像一座真正的、被人遗弃的废墟。我没看见他。
第二次去,是六七天后的傍晚。天阴沉沉的,飘着细碎的雨夹雪。那几块挡门的破木板好像被风吹倒了一块,豁口露出更大的黑洞。观前空荡荡的,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只有冰冷的雨雪,无声地落在瓦片上,落在空地上,落在那些没清理干净的碎屑上。
他没出来。也不知道是伤还没好,不能动,还是……根本不在里面。
我站了一会儿,雨雪打湿了额发,冰凉的水珠顺着脸颊往下淌。怀里那个旧布袋贴着心口,没什么动静,只是冰凉一片。
我转身往回走,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盼头,也像这雨雪一样,一点点冷了下去。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,转眼入了冬。第一场真正的雪落下来,不大,薄薄地盖了一层,把村子里的污秽和道观那边的破败,都暂时掩埋在一片刺眼的苍白下面。
那天晌午,我娘在灶间腌酸菜,让我去地窖里再拿两颗白菜上来。地窖口在院子角落,用石板盖着,旁边堆着些柴火。
我掀开沉重的石板,一股混合着泥土和蔬菜味道的、凉飕飕的气息涌上来。我顺着木梯往下爬。地窖里光线昏暗,只有窖口透下来一点天光,勉强能看清堆放的萝卜、土豆和白菜的轮廓。
我弯腰去抱白菜,窖口的光忽然被挡住了一大半。
我以为是云遮住了太阳,没在意。抱起两颗冰凉的大白菜,转身想往上爬。
就在我抬起头,视线无意间扫过窖口时——
整个人僵住了。
窖口那块四方形的光亮里,映出一个人影的轮廓。
不是站在窖口边上,而是**正对着窖口,微微低着头,朝着下面看**。
光线从他背后照过来,看不清脸,只能看到一个戴着**斗笠**的、模糊的头部侧影,和肩膀的轮廓。斗笠边缘垂下一些,遮住了大半面容。
但那身衣服……洗得发白、几乎看不出本色的**玄青色**,即便在逆光里,我也认得。
是他。
他就那么静静地站在窖口,微微低着头,看着地窖下面的我。
没有声音,没有动作。
像一尊突然出现在那里的石像。
我抱着冰凉的白菜,仰着头,僵在昏暗的地窖里,心跳都停了一拍。地窖里阴冷的气息包裹着我,我却觉得一股麻意从脚底板直窜上天灵盖。
他……什么时候来的?来干什么?
找我?
为什么不出声?为什么不下来?或者……为什么不走开?
我们就这么一个在亮处,一个在暗处,隔着短短一段距离和昏黄的光线,无声地对峙着。时间像是被冻住了。只有地窖口飘下来的、细小的雪末,在那一方光亮里打着旋儿,慢慢落下。
我张了张嘴,想喊他,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,发不出声音。
就在这时,他动了。
不是走进来,也不是离开。
他只是微微侧了侧头,似乎是调整了一下角度,让窖口的光线能更好地落在他身上——或者说,落在他脸上。
然后,我看清了。
斗笠下的脸,依旧苍白消瘦,但比上次见到时,似乎有了点活气。眉心的伤口已经愈合了,留下一个暗红色的、凹凸不平的疤痕,像一小块烧融后又凝固的蜡,嵌在苍白的皮肤上,有些刺眼。除此之外,脸上很干净,没有血污,没有尘土。
他的眼睛,隔着那段距离和昏暗的光线,正**看着**我。
不是上次那种空茫的死寂,也不是更早之前那种深井般的平静无波。那双眼睛里,此刻清晰地映着窖口透下的天光,映着飘落的细雪,也映着……窖底昏暗光线里,仰着脸、抱着白菜、僵硬如木偶的我。
眼神很复杂。有审视,有估量,似乎还有一丝极淡的、说不清是疲惫还是别的什么的情绪。他就用这样的眼神,静静地、毫不避讳地,看了我好几息。
然后,他极轻微地,几不可察地,朝着我这边,**点了点头**。
幅度很小,只是下巴往下压了一瞬,随即又抬起。
没有笑容,没有说话,甚至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。
只是一个点头。
做完这个动作,他没再停留,转过身,身影很快从窖口那方光亮里移开,消失了。
窖口重新变得空荡荡,只剩下飘落的雪末和清冷的空气。
我依旧僵在原地,仰着头,望着那块重新变得只有天光的窖口,怀里抱着的白菜冰冷沉重。
刚才……是真的吗?
他来了?就为了站在窖口,看我一眼,然后……点个头?
什么意思?
是谢我?还是别的什么?
那眉心狰狞的疤……是永远留下了吗?
无数个问题在脑子里冲撞,却得不到任何答案。
地窖里的阴冷让我打了个哆嗦。我这才回过神,抱着白菜,手脚并用地爬上木梯。
爬出地窖,院子里白茫茫一片,薄雪上干干净净,只有我下来时踩出的一串脚印。院门外,通往村尾的小路上,也空无一人,只有风吹着雪末,打着旋儿。
他走了。像他来时一样,悄无声息。
我抱着白菜,站在雪地里,望着村尾方向。道观被低矮的房屋和光秃秃的树杈挡着,看不见。
只有怀里白菜冰凉的触感,和眉心那块皮肤下,似乎又隐隐开始**发烫**的错觉,提醒我刚才并非幻觉。
我娘在灶间喊我:“白菜拿来了没?磨蹭什么呢!”
我应了一声,抱着白菜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灶间。冰冷的白菜贴近胸口,那里,旧布袋的存在感,忽然变得无比清晰。
雪还在下,细细的,密密的,不紧不慢,要把一切都覆盖成同一种颜色。
我放下白菜,走到窗边,望着外面越来越密的雪幕。
他来了。
又走了。
只留下一个点头,一个疤,和更多理不清、道不明的纠缠。
这因果,怕是真要缠一辈子了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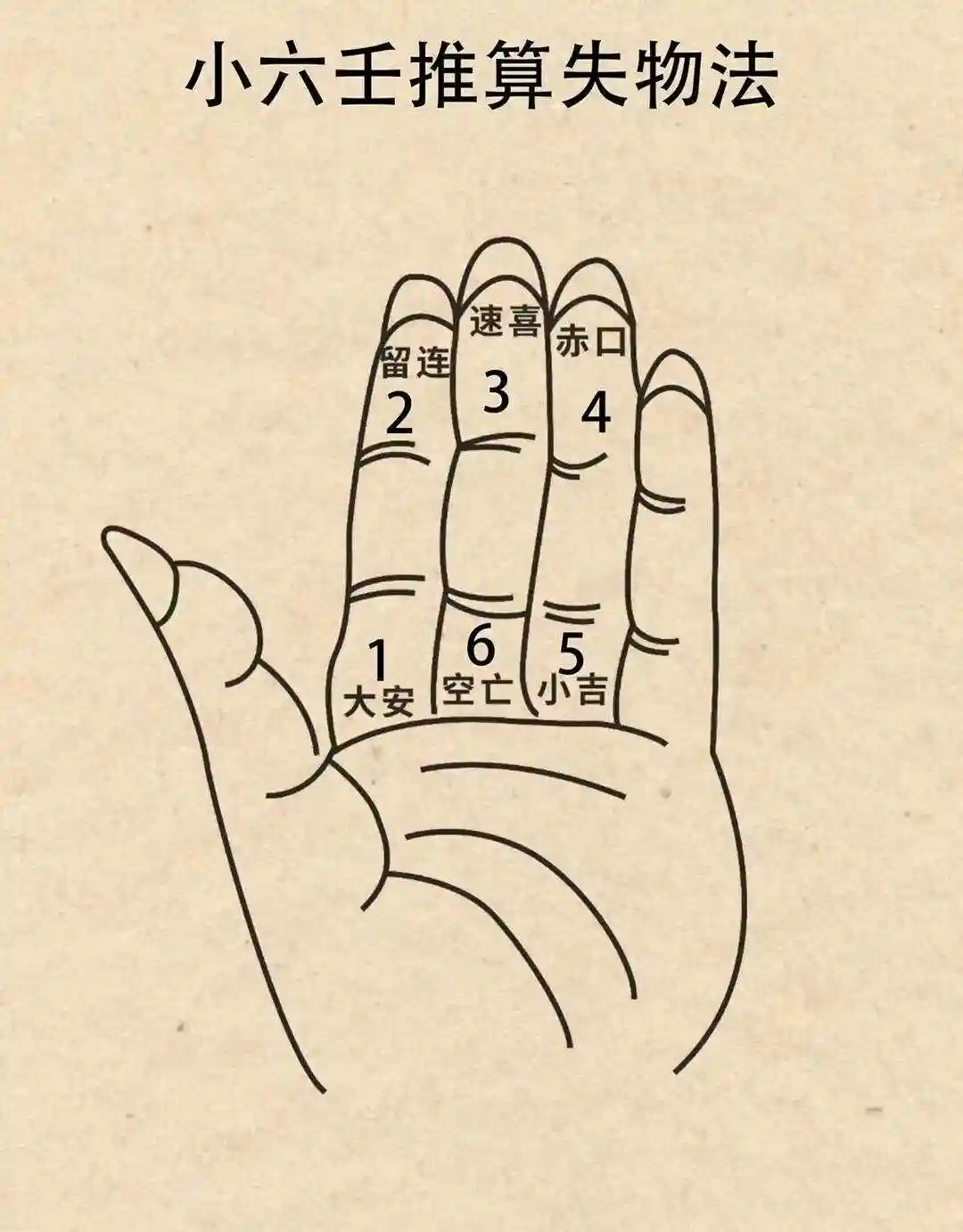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