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定城西有棵唐槐,三个人合抱那么粗,树心都空了,可枝叶还茂盛。树下住着个柳媒婆,说媒四十三年,成就三百对姻缘。
柳媒婆说媒有个怪癖:必带人去老槐树下相看。两人往树前一站,她眯眼看看,便知成不成。问她怎么看出来的,她指指树梢:“瞧见没?树上住着位‘槐仙奶奶’,专管姻缘。她若中意,就摇摇叶子;不中意,叶子纹丝不动。”
人都当她说笑。可那年秋分,城里绸缎庄的少东家陈明轩,偏不信这个邪。
陈明轩留过洋,信的是“自由恋爱”。家里给说了十几门亲,他个个瞧不上。陈老爷急了,押着他来找柳媒婆。
柳媒婆领他到槐树下,唤来城南苏绣坊的姑娘苏婉清。两人站定,柳媒婆仰头看树——怪了,往常微风就簌簌响的槐叶,这会儿静得像画上的。
柳媒婆心里咯噔一下,面上却笑:“槐仙奶奶今日乏了,改日吧。”
陈明轩本就敷衍,拱拱手走了。可夜里做了个梦:梦里槐树下站着个蓝衣老太太,用拐杖敲他膝盖:“小洋鬼子,瞧不上我们婉清?她前世是我树下烧香的丫头,我等了她三世姻缘!”
陈明轩惊醒,腿上真有一块青。
隔日鬼使神差,他竟去了苏绣坊。苏婉清正在绣架前飞针走线,绣的是幅“槐荫送子图”。见他来,脸一红,针扎了手。
血珠滴在绣布上,正好染红送子娘娘手里的线。陈明轩忙掏手帕,四目相对,心里“咚”地一跳。
再去槐树下,风一吹,满树叶子哗啦啦响,像在拍手笑。
亲事就这么定了。成亲那日,花轿特意绕到槐树下。柳媒婆看见轿顶落了片槐叶,青翠翠的,摘下来给新娘子戴在鬓边:“槐仙奶奶给的压轿福。”
小两口和美。第三年苏婉清有孕,临盆时却难产。稳婆出来摇头,陈明轩冲到槐树下,“砰砰”磕头:“槐仙奶奶救救我妻儿!”
磕到第九个,树洞里飘出个蓝衣老太太虚影,往陈家方向去了。稳婆后来跟人说:“怪了!眼看见不行了,忽然闻见股槐花香,孩子‘咕咚’就出来了。”
孩子满月,陈家去槐树下还愿。发现树身空洞里供着个褪色的绣花鞋——正是当年苏婉清前世做丫头时,在树下遗落的。
如今那棵唐槐还活着,成了姻缘树。年轻男女去挂红绳,若见槐叶无风自动,便是好兆头。柳媒婆早不在了,可她孙女接了班,说媒前还是必到树下站站。
有人问灵不灵,她就笑:“你瞧我奶奶活到九十三,说媒说到九十三——若不是槐仙奶奶帮着,哪来这么多好姻缘?”
二十七、渡口的无头船夫
松花江有个老渡口,摆渡的是个疤脸老汉,姓甚名谁没人知道,只唤他“老摆渡”。他摆渡四十年,有三不渡:雨夜不渡、孕妇不渡、戴孝者不渡。
这年七月十五,鬼节。天擦黑时来了个穿白衣的女人,抱着个包袱要过江。老摆渡摆摆手:“今日不渡。”
女人跪下哭:“船家行行好,我娘病重,等我送药。”
老摆渡看她包袱缝里露出的真是药草,心一软:“上船吧,莫回头。”
船到江心,女人忽然问:“船家,你听说过无头船夫的故事吗?”
老摆渡手一抖:“客官莫说这个。”
女人自顾自说:“说是四十年前,这渡口有个年轻船夫,七月十五那夜渡了个穿白衣的孕妇。船到江心,孕妇忽然变成青面獠牙的恶鬼,一口咬掉了船夫的头……”
老摆渡的篙“啪”地掉在船上。
女人慢慢转头——月光下,她的脖子有道细细的红线:“那船夫就是我爹。他被恶鬼夺了头,怨气不散,成了这江里的无头鬼,专在七月十五找替身。”
她解开头巾,头颅竟提在手里!“船家,你看我像你当年渡的那个孕妇吗?”
老摆渡忽然笑了,笑声嘶哑。他伸手在脸上一抹——那张疤脸皮掉下来,露出没有头颅的脖颈!脖颈上张开一张嘴说话:
“闺女,你找错人了。我就是那个无头船夫。”
他撩起衣摆,腰间挂着颗干瘪的人头:“这才是我的头,当年被恶鬼咬掉后,我抢回来了。可怨气太重,入不了轮回,只好在这摆渡赎罪。四十年来,我救了十七个落水者,超度了三十八个水鬼——还差一个,就能解脱了。”
他把头颅转过来,对着白衣女鬼:“你,就是第四十九个。”
女鬼尖叫一声要逃,老摆渡从怀里掏出枚生锈的船钉,“噗”地钉在船板上。江水忽然沸腾,无数苍白的手伸出水面,抓住女鬼往下拖。
“你爹当年贪财,明知七月十五鬼门开,还收恶鬼的银钱摆渡。”无头船夫的声音从腰间头颅传出,“害我丢了头,也害他自己被恶鬼吞了魂魄。今日我超度你,算是了结这段冤债。”
女鬼沉入江底前,忽然哭了:“船家……我爹的坟在江东第三棵柳树下……若你解脱了,替我说声对不起……”
江面恢复平静。老摆渡把脸皮贴回去,摇船回岸。第二天,渡口换了新船夫——是个脸上有疤的年轻人,说昨夜梦见个无头老汉传他摆渡手艺,还托他去江东柳树下烧纸。
新船夫也立下三不渡的规矩。有雨夜过江的,隐约能听见老船夫的号子声;有孕妇临产,总梦见无头人撑船来接;至于戴孝者——七月十五那夜,渡口会无缘无故多出艘空船,船上摆着香烛纸钱。
老人说,那是老摆渡在收“渡资”。收满了,他就能找回自己的头,重新做人了。
二十八、画皮匠的最后一笔
京城琉璃厂有个画皮匠,姓秦,专给戏班子画脸谱,也给死人画遗容。他画的遗容,能让人像睡着一样安详。
秦师傅有支朱砂笔,传了七代,据说笔毛是黄大仙的尾尖毫。他临终前想传笔,可独子早夭,只剩个八岁的孙女小莲。
这年腊月,城东棺材铺送来具无头尸,是刑场上斩的江洋大盗。家属求秦师傅画个全尸,好下葬。秦师傅本不想接——无头尸怨气重。可家属跪着哭,他心软了。
对着空脖颈,他调了七天颜料。第八天夜里,正画到喉结处,油灯忽明忽暗。秦师傅抬头,看见镜子里自己身后站着个黑影,脖颈处鲜血淋漓。
“秦师傅……给我画俊些……”黑影声音空洞。
秦师傅稳住手:“放心,让你体体面面走。”
画到鸡叫三遍,成了。尸身脖颈上长出张俊朗的脸,只是闭着眼。秦师傅累极,伏案睡了。
梦里那黑影又来了,这回有了头,正是他画的那张脸:“秦师傅好手艺……可我舍不得这身子……借我用用可好?”
秦师傅惊醒,发现那尸体的手动了!正抓住朱砂笔往脸上添眼睛——点睛,魂就锁在尸身里了!
他扑上去抢笔,可八十岁的老人哪抢得过?眼看笔尖要点上瞳孔,八岁的小莲突然冲进来,咬破手指,“啪”地把血抹在尸体额头上。
尸体惨叫一声,瘫软下去。朱砂笔掉在地上,笔毛焦了一半。
小莲扶起爷爷:“爷爷,我看见……看见它从镜子里爬出来……”
秦师傅老泪纵横,抱住孙女:“咱家的笔……该传给你了。”
三日后秦师傅去世,小莲成了最小的画皮匠。她接的第一单,就是给爷爷画遗容。画时总觉得爷爷在教她:“眉要淡,唇要暖,苦命人要画点笑……”
那支焦了笔毛的朱砂笔,她供在祖师爷牌位前。说来也怪,凡她画的遗容,家属都说死者托梦说满意。
十七岁那年,她给个溺死的姑娘画容。姑娘脖颈有掐痕,分明是他杀。小莲画着画着,笔自己动了——在姑娘手心画了朵梅花,梅心三点朱砂。
官府据此抓到真凶:正是姑娘的未婚夫,手上有梅花胎记。他说掐死姑娘时,姑娘用指甲在他掌心抠了三道血痕。
小莲名声大振。可她也立下规矩:横死者不画全容,留一笔给阴司判;冤死者必留记号,等天理昭昭。
如今琉璃厂还有秦家画铺,当家的是个老太太,九十岁了手不抖。有人问那支焦笔的来历,她就指指墙上黄大仙的画像:“祖师爷赏饭吃,也管着饭——心不正,笔自焚。”
夜里关铺时,她总对着空屋子说一句:“爷爷,今日画了七个,都体面。”有学徒说,听见过老头的咳嗽声,像在答应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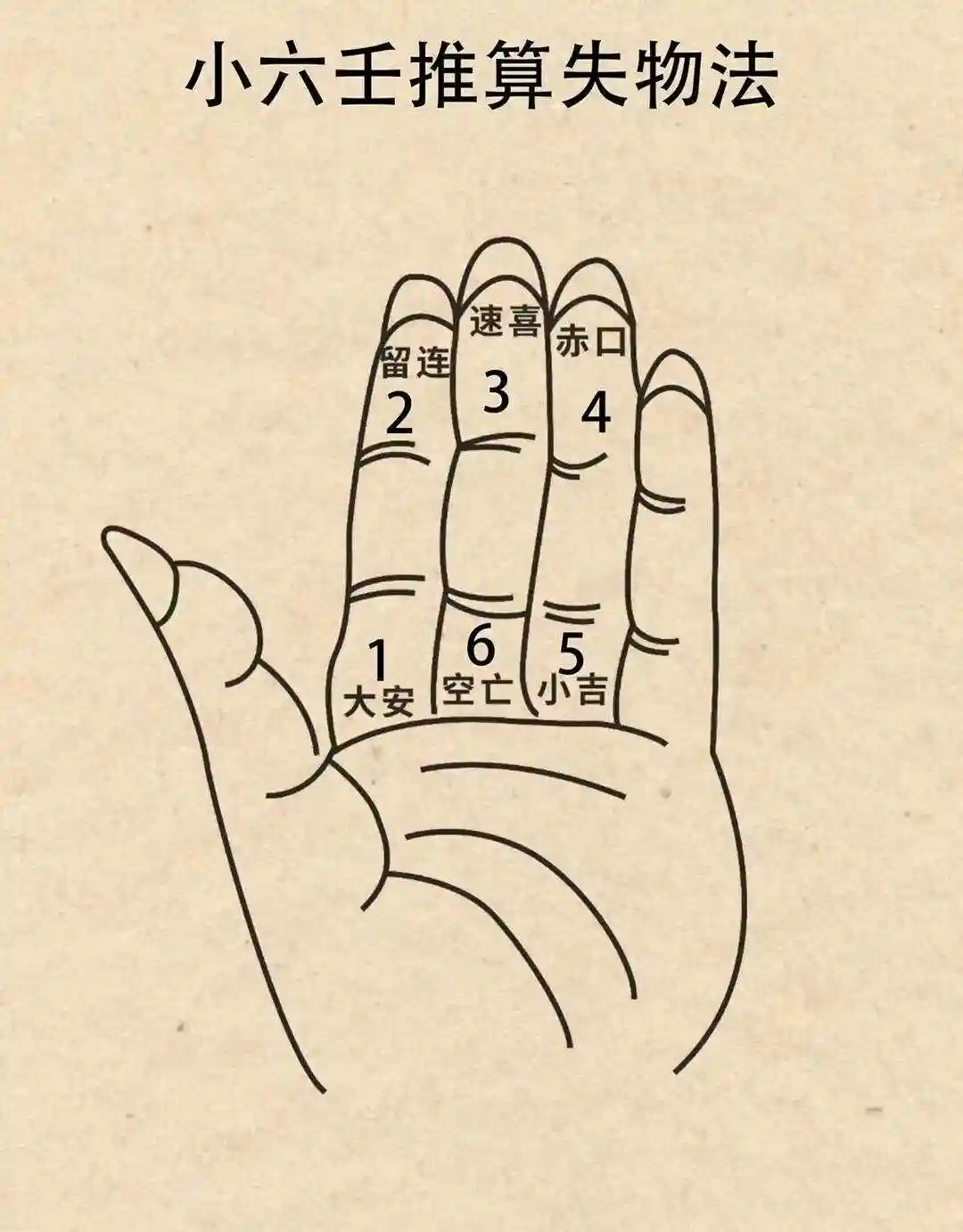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