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时三刻,整座城市只有一家店还亮着灯笼。
灯笼上写着“当”字,却不是寻常当铺。门联上联是:“典金典银典身外物”,下联是:“当命当运当心头血”。横批四个字:“来者不拒”。
我站在门口,捏着口袋里最后三枚硬币。失业第七个月,房东明天就要换锁。
推门时,风铃不响。
一、柜后的女人
柜台很高,我只能看见一双涂着鲜红蔻丹的手,正在拨弄算盘。
“当什么?”声音慵懒,像刚睡醒。
“我……没什么值钱的。”我窘迫道。
红指甲的手停了。一张脸从柜台后抬起——是个极美的女人,三十上下,眉眼如画,但眼神像结了冰的湖。
“你有三年阳寿,”她红唇轻启,“当不当?”
我笑了:“老板娘别开玩笑。”
她也笑了,从抽屉里取出一面铜镜,推到我面前。镜中不是我,是个垂垂老矣的老翁,满脸褐斑,气若游丝。
“这是三年后的你,”她指尖轻点镜面,“若今夜你冻死街头,镜中便是你七十岁时的模样。若你活到七十……少这三年,也不打紧。”
我盯着镜中老翁的眼睛——那眼神里的绝望,和此刻的我如出一辙。
“当了能换什么?”
“换一双眼睛,”她凑近,身上有冷香,“看透财气的眼睛。金银珠宝在你眼中会发光,财位吉地在你眼中会生雾,身怀横财的人……头顶有金云。”
二、第一个夜晚
契约签在无字黄绢上,我按血手印时,绢上浮现金色符文,随即消失。
女人递给我一盏白灯笼:“提着它,走出去。灯笼灭时,眼睛就开了。”
我走出当铺,灯笼无风自亮。穿过三条街,拐进出租屋所在的暗巷时,灯笼“噗”地灭了。
世界变了。
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光尘,有的地方浓如晨雾,有的地方稀薄如纱。我住的那栋破楼,整栋漆黑——没有一丝光尘。
而隔壁那栋老宅院,屋檐上蒸腾着淡金色的雾气,像刚揭开的蒸笼。
三、金雾的秘密
我鬼使神差地走到老宅门前。透过门缝,看见院里那棵老槐树下,埋着个陶罐,罐口溢出浓郁的金光。
“谁在外面?”门内传来苍老的声音。
门开了,是个穿汗衫的老头,手里拿着蒲扇。
我脱口而出:“您家树下……有东西。”
老头眼神骤变。他盯着我看了半晌,缓缓侧身:“进来说。”
那夜,我在老槐树下挖出一个清代咸菜坛,里面装满银元,还有两根小黄鱼。老头姓周,独居,他说这是他太爷爷藏的,家传的口诀失传了,找了几十年。
“你怎么看见的?”他问。
我指了指自己的眼睛。周老头沉默良久,从坛里取出五枚银元给我:“封口费。”
又取出一根小黄鱼:“再帮我看个地方。”
四、赌石的诱惑
周老头带我去的是城南玉器街。他说年轻时在这条街当学徒,总觉得有家店“不对劲”。
“荣石斋”,百年老店。我站在店门口,看见整间店铺笼罩在翡翠般的绿光中,而最亮的光源——来自墙角那块蒙尘的镇纸石。
“那块石头,”我压低声音,“里面有货。”
周老头花三千块买下“镇纸石”。切开时,全场寂静——满绿玻璃种,拳头大小,估价百万。
老板红了眼:“这石头在我店里三十年……”
周老头塞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。我数了,两万。
五、头顶的金云
有了钱,我先交了房租,然后开始在城市里游荡。
这双眼睛让我看见另一个世界:
银行金库在地下三层,金气却穿透地面,像金色喷泉;彩票站偶尔有人头顶有淡淡金云,我便跟着买几注——中过两次小奖;古玩市场的地摊下,埋着民国铜钱,我花五十块“捡漏”,转手卖五千。
但我渐渐发现,金云分三种:
淡白如雾的,是小财;金黄如穗的,是正财;而紫金如霞的……是横财,也是凶财。
六、紫金凶财
我在酒吧遇见第一个头顶紫金云的男人。四十多岁,西装革履,正在灌酒。他头顶的紫金云翻腾如沸,云中隐约有血色。
我坐到他旁边:“先生,最近发了一笔财?”
他猛地转头,眼神凶狠:“你谁?”
“能看见些东西的人。”我指了指他头顶,“这财……带血光。”
男人酒醒了三分。他盯着我,突然抓住我手腕:“你能看见?真能看见?”
他叫孙老板,做建材生意。半个月前,他的工地挖出古墓,工人私分陪葬品,他作为负责人,暗中收了几件最值钱的青铜器。
“从那天起,我就没睡过安稳觉,”他眼睛布满血丝,“一闭眼就听见有人哭。”
我看着他头顶紫金云里的血丝:“东西在哪?”
七、青铜器的诅咒
东西藏在孙老板郊区别墅的地下室。开门瞬间,我被浓烈的黑气冲得倒退三步——那不是财气,是死气。
三件青铜器摆在供桌上,其中一件鼎,表面凝结着暗红色的“霜”。
“这不是霜,”我凑近看,“是血沁……千年血沁。”
孙老板瘫坐在地:“怎么办?”
“物归原主。”我说,“从哪里挖的,埋回哪里去。但要选时辰——明夜子时,月掩金星时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这么多?”
我摸着自己的眼睛:“这双眼睛……看得见该埋在哪里。”
那夜,孙老板头顶的紫金云散了。
三天后新闻播报:某建筑工地发现汉代古墓,考古队已介入保护。孙老板作为“热心市民”受表彰。
他送来一个手提箱,里面是二十万现金。
“这是封口费,”他说,“也是救命钱。”
八、当铺老板娘再现
我带着二十万再次来到午夜当铺。
灯笼还亮着,门却推不开。门上贴了张纸条:“典当之物,概不赎回。”
“老板娘!”我拍门。
门内传来她的声音,隔着门板,闷闷的:“你的眼睛用得可好?”
“我想赎回来!我的三年阳寿!”
里面沉默良久。门开了一道缝,递出一面铜镜。
镜中还是那个垂死老翁,但额头上多了一道金线,像第三只眼的轮廓。
“看见了吗?”老板娘的声音带着笑意,“眼睛已经长在你命里了。强行剥离,你会立刻变成镜中模样。”
我手一抖,镜子差点落地。
“不过,”门缝里的红指甲勾了勾,“你可以继续当。再当三年阳寿,这双眼睛……能升级。”
九、升级的眼睛
我当了。
第二次契约签完,眼睛灼痛如火烧。再睁开时,世界更清晰了:
我能看见“财脉”——地下的金银会显出光脉,像树根一样延伸;能看见“财劫”——那些注定破财的人,财气上有裂痕;甚至能看见“财运流转”——金云从一个人头顶飘向另一个人的轨迹。
我用这双眼睛做起了“财运顾问”。
富商王总请我看新买的别墅。我指出地下室是“财库漏穴”,建议改成酒窖聚气。三个月后,他谈成一笔搁置两年的生意。
珠宝店李老板请我调整柜台布局。我让他在东南角摆流水摆件,引动“财水”。当月营业额涨了三成。
钱像雪片一样飞来。我在最好的小区买了房,开上了曾经不敢想的车。
但镜中的老翁,每照一次,就更老一分。
十、最后的客人
第八个月,来了个特殊的客人。
是个七八岁的小女孩,穿洗得发白的裙子,手里攥着三枚硬币。她站在当铺门口,仰头看灯笼。
“小朋友,这里不是玩的地方。”我正要关门——那天老板娘不在,我临时看店。
“我爷爷要死了,”小女孩声音细细的,“他们说,这里能救命。”
我心里一紧。
“你爷爷……怎么了?”
“病了,没钱治。”她把三枚硬币放在柜台上,“我能当什么?当我的命行吗?我分一半给爷爷。”
我看着她头顶——没有金云,只有一团温暖的、乳白色的光,那是孩童才有的纯净生气。
“这里不收你的东西。”我把硬币推回去,又从抽屉里取出一沓钱——是孙老板给的二十万里剩下的,“拿去吧,给你爷爷治病。”
小女孩愣愣地看着我,又看看钱。
“叔叔是好人,”她小声说,“爷爷说,好人头顶有白光。我看见了,叔叔头顶也有,虽然……旁边有点黑。”
我浑身一震。
她看得见?
十一、眼睛的代价
小女孩走后,我第一次认真看镜子。
镜中的老翁,头顶确实有一圈极淡的白光——是我的本命生气。而白光周围,缠绕着丝丝黑气,像藤蔓一样勒紧。
那是使用“财眼”的代价:每看一次财气,就损耗一分生气;每指点一次财运,就沾染一分因果。
我帮孙老板避祸,黑气里就多了古墓亡魂的怨念;我帮王总聚财,黑气里就多了他竞争对手的诅咒。
这双眼睛,在让我暴富的同时,正慢慢绞死我。
十二、子时的选择
老板娘回来了,带着一身夜露的寒气。
“想赎眼睛了?”她似笑非笑。
“不,”我听见自己说,“我想当最后一样东西。”
“你还有什么可当的?”
“我剩下的全部阳寿,”我说,“换这双眼睛……彻底消失。”
老板娘拨算盘的手停了。
“想清楚了?没了这双眼睛,你会变回原来的穷光蛋。而且……你已损耗的阳寿,回不来了。”
“想清楚了。”
契约第三次签下。这次,黄绢上的金色符文亮如熔金。
签完字,我眼前一黑。
十三、寻常人间
再醒来时,我在出租屋的床上。口袋里只有三枚硬币,手机里是房东的催租短信。
窗外阳光刺眼。
我走到镜子前——镜中是二十八岁的我,眼角有了细纹,鬓角有了白发。比实际年龄老了些,但至少,是个活人。
空气里没有光尘,老宅没有金雾,行人头顶没有金云。
世界恢复了它原本的、平淡的样子。
我花最后一枚硬币买了馒头,边啃边找工作。下午,我接到电话——是周老头。
“小子,怎么这么久没联系?”他在那头笑,“我那个银元坛子,卖了不错价钱。缺钱不?先借你点。”
我怔住了。
“还有,我外甥的公司招人,我觉得你挺机灵,推荐你了。明天去面试?”
挂掉电话,我看着手里半个馒头,突然笑了。
原来,没有那双眼,人间照样有暖意。
十四、灯笼再亮
三个月后,我还清了债务,有了份稳定工作。路过那条巷子时,我总会绕开。
直到某个雨夜,我抄近路回家,又看见了那盏灯笼。
灯笼亮着,门上贴了新纸条:“招夜间看店,薪资面议。”
鬼使神差地,我推门进去。
柜台后坐着个小女孩——是当初那个要用命换爷爷的小女孩。她穿着新裙子,头顶的乳白光晕更暖了。
“爷爷病好啦,”她冲我笑,“老板娘让我在这里等她。叔叔,你要当东西吗?”
我摇头,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给她——这是我最近的习惯,口袋里总备着糖。
“叔叔,”小女孩接过糖,突然说,“你头顶的白光,比以前亮多啦。”
我一愣。
“虽然还是很淡,”她歪着头,“但是,不黑了。一点黑气都没有了。”
风铃响了。
老板娘从里间走出来,红裙摇曳。她看看小女孩,又看看我,唇角勾起。
“回来了?”她像在问家常。
“嗯,”我说,“回来看看。”
“看店的工作,做不做?”她递过一张新契约,“这次不当阳寿,当时辰。每晚子时到寅时,月薪……够你生活。”
我接过契约,上面没有金色符文,只有普通的钢笔字。
“这次……当什么?”
“当你的善念。”老板娘抱起小女孩,眼神难得温和,“每值一夜班,店里收你一份善念,存在这孩子的命格里。等她长大,这些善念能保她一生平安喜乐。”
我看着小女孩清澈的眼睛,在那双眸子里,看见了自己头顶淡淡的、干净的白光。
“好,”我说,“我当。”
风铃又响,有客来了。
小女孩跳下柜台,跑去开门。门外站着个憔悴的年轻人,口袋里只有三枚硬币。
“请进,”我听见自己说,声音平静,“本店典当,来者不拒。”
灯笼在雨夜里,暖得像一颗不会熄灭的星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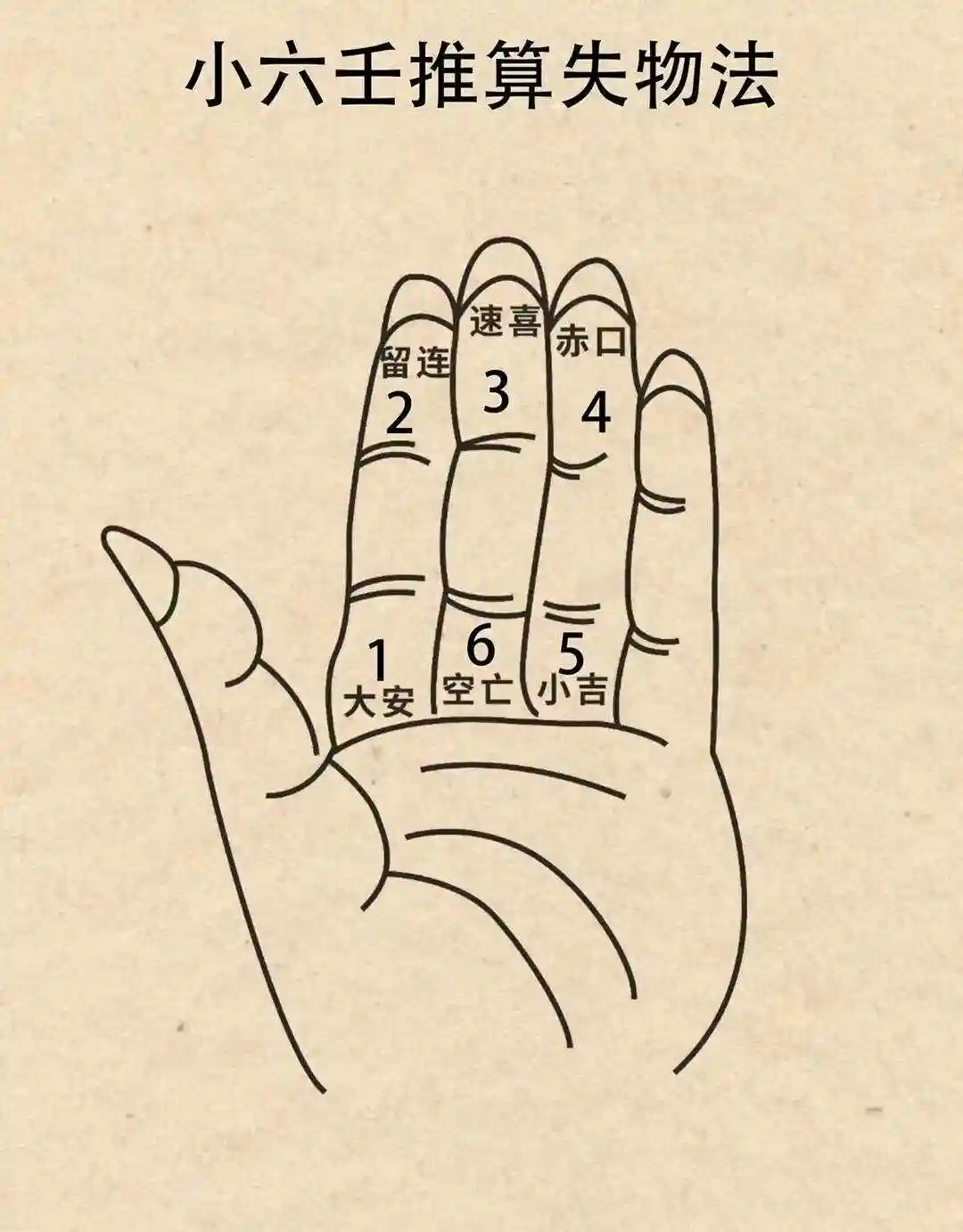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