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光青白,斜斜地照进来,浮尘在光柱里慢慢打转。外头村子有了响动,远远近近的鸡鸣,几声犬吠,还有谁家开门,“吱呀”一声,隔了这么远,竟也隐隐约约听得见。
人间醒了。
可我看着他靠在那里的样子,却觉得离那人声烟火气隔了千山万水。他脸上一点活气都没有,白得像供桌上那尊掉光了彩的泥胎,只有眉心那点暗沉,固执地杵着,衬得脸色更瘆人。那身道袍,血污板结成一块块深褐,硬邦邦地裹在身上,看着都觉得难受。
他说“走”,可那模样,哪里像是能自己走出去的。
我心里慌,又不敢贸然上前。刚才渡气时的滚烫触感,还有他醒来后说的那些“炁”、“地脉”之类听不懂的话,都让我觉得,眼前这个人,虽说是救了我(大概也算救了吧),却比门外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,更让人心里没底。
我攥着那没用的旧布袋和废符,指甲抠进掌心烫伤的皮肉里,一阵刺痛,才让我稍稍定神。
他闭着眼,胸膛的起伏微弱而平稳,像是在积蓄力气,又像是单纯地懒得动弹。天光渐渐移到他身上,照出他紧抿的、毫无血色的唇线。
“道长,”我嗓子干得发紧,声音细得自己都快听不见,“你……能走吗?”
他眼睫动了一下,没睁眼,只极轻微地摇了摇头。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,但意思明明白白。
不能。
那怎么办?总不能一直待在这破观里。昨夜那些东西是退了,可谁知道还会不会再来?再说,他伤成这样,不请郎中,不吃药,光躺着能行吗?
我咬着下唇,看看他,又看看门外渐亮的天。村子就在那边,跑回去喊人?可怎么跟人说?说他为了救我,弄得满身是血,还引来了不干净的东西?谁会信?昨夜那骇人的经历,如今在青天白日下回想,都像是场荒诞的噩梦,说出来只怕要被当成失心疯。
正六神无主,他忽然开了口,眼睛依旧闭着,声音低得像呓语。
“柜子……后面……”他喘了口气,才接上,“有个暗格……里面……有药,红色的瓶子……还有……干净的布。”
我愣了一下,顺着他之前目光无意扫过的方向看去,是供桌旁边一个歪斜的、掉了漆的旧木柜,堆在墙角,落满了灰,像是几十年没动过。
我爬起来,腿脚还是软的,趔趄了一下才站稳。走到那柜子前,灰尘呛得我想咳嗽,又硬生生忍住。柜子很沉,我使了吃奶的力气,才把它从墙边挪开一点,露出后面斑驳的墙面。
暗格?哪里有什么暗格?
我用手在墙上摸索,砖石粗糙冰冷。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,指尖触到一块略微松动的砖。心里一动,我试着用力往里按,没反应。又试着往旁边推——
“咔哒。”
一声极轻微的机括响动,那块砖竟向内陷进去半寸,然后旁边两块砖无声地滑开,露出一个黑黢黢的、巴掌大的方洞。
真的有!
我心跳又快了起来,伸手进去摸索。洞里不深,指尖很快碰到几个冰凉的东西。我小心翼翼地拿出来,是两个小瓷瓶,一红一白,还有一个油纸包,里面裹着一小卷看起来还算干净的素白棉布。
我拿着东西回到他身边,蹲下来,把东西一样样摆开。红色瓷瓶的塞子很紧,我拔了几下才拔开,一股浓郁的药味冲出来,有点辛辣,又带着点苦。里面是些暗红色的药粉。白色瓷瓶里是几颗龙眼核大小的黑色药丸,气味淡些,有点草木清香。
“红的,”他依旧没睁眼,声音更弱了,“外敷。白的,一颗,内服。”
我看着他身上那件几乎和伤口粘在一起的道袍,手足无措。“可……你的衣服……”
“……撕开。”他言简意赅。
我吸了口气,手指颤抖着,去碰他腰侧一处颜色最深的血迹。布料又硬又脆,浸透的血干涸后,几乎成了铠甲。我不敢用力,怕扯到伤口,试了几次,只在边缘撕开一个小小的口子。
他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。
“直接……倒上去。”他像是耗尽了耐心,或者力气,语速快了点,“快点。”
我一咬牙,拔开红瓶塞子,对着那道撕开的小口,将里面暗红色的药粉倒了进去。药粉接触到血污板结的布料,没什么反应。我又抖了一些在周围其他几处深色血渍上。
然后,我拿起那卷白布,却不知从何下手。他浑身都是伤,这小小一卷布,够裹哪里?
他似乎知道我的为难,终于睁开了眼,目光落在我手里的布上,又移到我脸上。那眼神空茫茫的,没什么焦点,却让我觉得无所遁形。
“手。”他说。
我茫然地伸出手。
他费力地抬起自己那只相对干净些的左手,指了指我左手掌心——被三角符烫伤的地方,已经起了几个亮晶晶的水泡,周围一片红肿。
“先包你的。”他说完,又闭上了眼,仿佛这几个字已经用尽了他最后的力气。
我愣住了,低头看着自己掌心那片狼藉,又看看他满身的伤。鼻子忽然有点发酸。
我没再说话,用牙配合着右手,从布卷上扯下一条,胡乱缠在自己左手上,打了个笨拙的结。
做完这个,我才又看向他。白色药丸……内服。
我拿起白色瓷瓶,倒出一颗黑色药丸,凑到他嘴边。他微微张嘴,我将药丸放进他口中。他干涸的嘴唇擦过我的指尖,冰冷而粗糙。
他合上嘴,喉结滚动,费力地将药丸咽了下去,随即又是一阵压抑的呛咳,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病态的潮红。
等他平复下来,气息更弱了,眼睛也重新闭上,像是沉入了半昏迷。
天光越来越亮,道观里的一切都清晰起来,越发显得破败不堪。我和他,一个靠墙半死不活,一个蹲在旁边手足无措,身上都脏污狼狈得不成样子。
该走了。必须走了。
我看着那卷剩下的白布,心一横。不能这么耗下去。
我再次伸出手,这次不是试探,而是用力抓住他腰侧道袍被撕开的口子两边,闭上眼睛,猛地一扯!
“嗤啦——”
一声令人牙酸的布料撕裂声。干涸的血痂被硬生生扯开,底下露出模糊的血肉,颜色暗红发黑,边缘翻卷,看着触目惊心。昏迷中的他身体猛地一颤,闷哼一声,额头上冷汗涔涔而下。
我强忍着胃里的翻腾,不敢细看,抖着手将红瓶里剩下的药粉,一股脑全倒在那狰狞的伤口上。暗红的药粉覆盖上去,很快被渗出的少许新鲜血液浸湿,变成一种更深的、近乎紫黑的颜色。
然后,我用那卷白布,开始笨拙地缠绕他的腰腹。布料不够长,只能勉强裹住最严重的伤处,打了个歪歪扭扭的结。
做完这一切,我跌坐在地上,后背也全是冷汗。看看他,药粉敷上去后,他身体的颤抖似乎平息了些,只是眉头依旧紧锁,呼吸微弱。
我歇了片刻,攒起一点力气,再次挪到门边。那根昨夜几乎被撞断的门闩,孤零零地掉在地上。我拉开门。
清晨的空气清冷而干净,带着草木和泥土的气息,汹涌地扑进来,将观内残留的那点檀香和血腥味冲散不少。外面空地上,石阶上,只有几片被风吹过来的枯叶,干干净净,仿佛昨夜那铺天盖地的黑暗、抓挠和撞击,都只是我的一场幻觉。
村子就在下方不远,炊烟袅袅升起。
我走回他身边,蹲下,看着他苍白安静的脸。这次,没有再犹豫。
我伸出手,穿过他腋下,用力将他架了起来。他比看起来还要沉,全身的重量几乎都压在我身上。我踉跄了一下,咬紧牙关,半拖半抱,一步一步,挪向那扇敞开的、通往人间晨光的大门。
跨出门槛的瞬间,清晨的阳光毫无遮挡地落在我们身上,暖意驱散了最后的阴寒。我眯了眯眼,回头看了一眼。
破旧的道观静静矗立在晨光里,门内阴影浓重,看不清昨夜狼藉的地面,也看不清供桌上那尊沉默的神像。
只有门槛内缘,残留着几点深褐色的、洗不掉的血迹,像一只只冰冷的眼睛,注视着我们离开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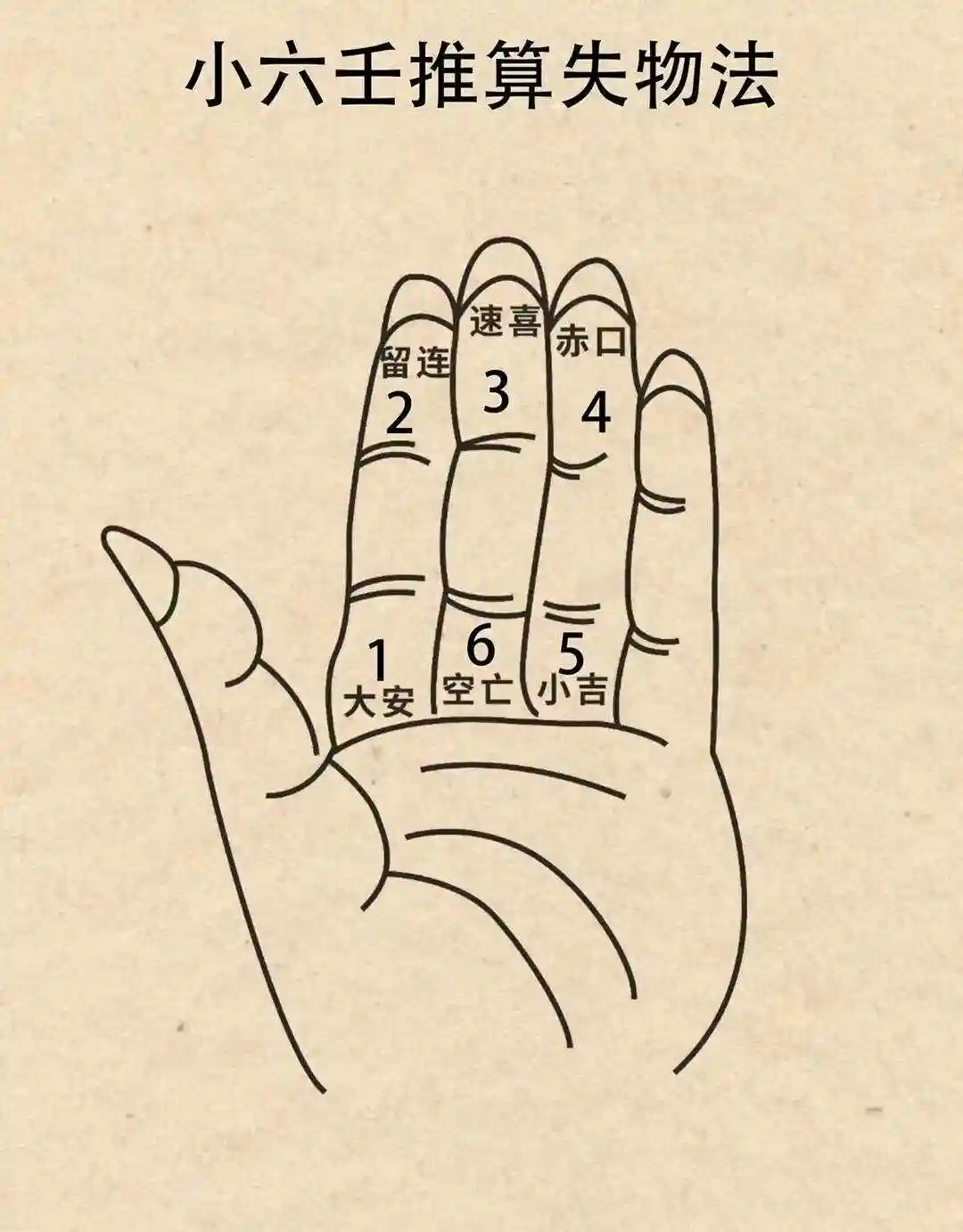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