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子就在眼前,几十步开外的土路,路旁歪斜的篱笆,早起捡柴的老汉佝偻的背影,都透着股活生生的烟火气。可架着他,这几十步路像是隔着一条河。他几乎整个人的重量都压在我半边身子上,沉得像灌了铅,脚拖着地,在土路上划出两道断断续续的浅痕。我咬着后槽牙,脖颈子上的青筋都迸出来了,才能勉强撑住不让他滑下去。
他头垂着,下巴抵在我肩窝,气息微弱,拂过我耳边的皮肤,带着药粉的苦味和血干涸后的铁锈气。眉心那点暗沉,在越来越亮的日头底下,反而更扎眼了,像滴永远擦不掉的墨。
有早起的村人看见了我们。先是隔着篱笆愣住,手里的柴火掉了一地。然后像是见了鬼,眼睛瞪得溜圆,张着嘴,半晌才发出一声变了调的惊呼:“哎——呀!”
这一声像是砸破了清晨的薄冰。更多的人从门里探出头,窗户后面挤着惊疑的脸。没人上前,都隔得老远,指指点点,交头接耳。那眼神,像看什么不祥的东西。
我喉咙发干,想喊人帮忙,却一个字也挤不出来。只能低着头,盯着脚下坑洼的土路,一步一步往前挪。汗水混着尘土,顺着额角往下淌,流进眼睛里,刺得生疼。左手掌心的烫伤被粗糙的布条磨着,火辣辣地疼。
终于挪到了我家那扇掉漆的木门前。门虚掩着,里头静悄悄的。我用肩膀顶开门,架着他跨过门槛。
堂屋里,我娘正背对着门,在灶台边舀水,嘴里还念叨着:“这死丫头,一晚上跑哪儿去了……”一转身,水瓢“咣当”掉在地上,水泼了一脚面。
她脸“唰”地白了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架着的人,又挪到我身上,嘴唇哆嗦着,半晌,才发出一声尖利的抽气:“我的老天爷!这……这是……道长?你们……你们这是……”
“娘!”我喊了一声,声音哑得自己都陌生,“快,帮忙!”
我娘这才像是醒过神,手忙脚乱地冲过来,想扶又不敢碰的样子。我们俩合力,总算把他挪到了我昨夜睡的那张小床上。床板发出不堪重负的“吱呀”声。
他一沾床,身体就软了下去,头歪向一边,再无动静。只有胸口极其微弱的起伏,证明还活着。血污和尘土立刻蹭脏了素色的床单,晕开一大片污渍。
我娘捂着嘴,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“造孽啊……这……这是怎么了?啊?昨晚上不是……道长不是救了你吗?怎么他自己……”她语无伦次,又猛地抓住我的胳膊,上下打量,“你呢?你伤着哪儿了?这一身的血……”
“我没事,娘,都是道长的血。”我挣开她的手,胡乱抹了把脸,“爹呢?”
“你爹一早就去邻村请王郎中了!说你昨晚……昨晚……”她想起昨夜我濒死的样子,又看看床上气息奄奄的人,更是六神无主,“这……这可怎么好!王郎中也未必……”
“先弄点热水,干净的布。”我打断她,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强硬,“再……再熬点稀粥,要清一点的。”
我娘愣了一下,看着我,像是第一次认识自己闺女。她没再多问,转身去了灶间,传来锅碗碰撞的慌乱声响。
我拖过屋里唯一一张破凳子,坐在床前。这才有空仔细看他。近距离看,更加触目惊心。脸上除了惨白,还有几道细小的刮伤,沾着尘土。嘴唇干裂得起了皮,泛着青灰色。最要命的是腰间我胡乱裹上去的白布,已经被渗出的血和药粉染透,变成了深褐色,硬邦邦的一坨,看着就觉得难受。
我娘端了盆热水进来,手里攥着块半新的软布,眼睛还是红的。“丫头,这……这男女有别,我……”
“娘,给我吧。”我接过布,浸在热水里拧了个半干。
我知道她顾忌什么。可眼下顾不上了。我娘守旧,胆子又小,指望不上。我定了定神,伸手去解他腰间那个被血污粘住的布结。结打得太紧,又浸透了血,根本解不开。我只能用热水浸湿的布巾,一点点去捂软它。
布巾的热气蒸腾起来,混合着血腥、药味和他身上一种凛冽的、像雪后松针的气息,扑在我脸上。我屏着呼吸,小心翼翼地动作。好不容易,布结松动了些,我慢慢解开,露出了底下狰狞的伤口。
昨夜灯光昏暗,后来又一片漆黑,看不真切。此刻在白天里,那伤口的模样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不是刀砍斧劈那种整齐的伤口,而是一片模糊的、暗红发黑的皮肉,边缘不规则地翻卷着,深处隐隐能看到一点森白的颜色。药粉覆盖在上面,糊成一团,和血污混在一起。
我娘在旁边瞥了一眼,立刻扭过头去,捂着嘴干呕了一声。
我手有点抖,但没停。用湿布巾蘸着温水,极轻极轻地去擦拭伤口周围已经板结的血污和药粉。我不敢碰伤口中间,只清理边缘。每擦一下,昏迷中的他似乎都有细微的颤动,眉头拧得更紧。
换了好几盆水,才勉强把伤口周围清理出点样子。我拿起昨夜从他暗格里带出来的白色瓷瓶,倒出一颗药丸,想喂他,可他牙关咬得紧。试了几次,药丸都被顶了出来。
“得用水化开。”我娘在身后小声说,递过来一个小瓷勺和半碗温水。
我把药丸放在勺子里,用温水慢慢滴上去,看着它一点点化开,变成深褐色的药汁。然后,我一手小心地托起他的后颈,让他头微微仰起,另一只手将勺子凑到他唇边,一点点将药汁喂进去。还好,这次他喉咙本能地吞咽了几下,大部分药汁都咽了下去。
做完这些,我已经出了一身汗,里衣都贴在了背上。看着那块没法再用的脏布,和我娘拿来的另一块干净棉布,我又犯了难。
我娘看看我,又看看床上的人,一跺脚,转身从柜子里翻出一件我爹的旧褂子,灰扑扑的,洗得发白,但还算干净。“用这个,撕了。”她把褂子塞给我,“总……总得裹上。”
我接过褂子,布料粗糙厚实。我用力撕开,扯成几条宽一些的布带。然后,用这些布带,重新将他腰间的伤口包扎起来。这次,我尽量包得平整些,不敢太紧,怕勒着他,也不敢太松,怕布带滑脱。打完结,我看着那被灰布覆盖的伤处,虽然依旧能看出渗血的轮廓,但总算比之前那血糊糊的一团像样点了。
我娘已经熬好了粥,稀薄得能照见人影,晾在一边。她看着床上的人,忧心忡忡:“这……光喂点水米,能行吗?伤得这么重,得请郎中瞧啊!”
“爹不是去请王郎中了吗?”我说,眼睛没离开他的脸。喂了药,清理了伤口,可他脸上那点微弱的活气,似乎并没有增加多少。呼吸依旧又轻又浅,眉心那点暗沉,在透过窗纸的日光下,幽幽地透着股冷意。
“王郎中……”我娘嗫嚅着,“也就治个头疼脑热,这……这可是要命的伤,我看悬。”
正说着,外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说话声。是我爹,带着王郎中回来了。
王郎中进了屋,先是被屋里的血腥气和床上的人惊得后退半步,待看清床上人的脸,更是“哎哟”一声:“这……这不是村尾的道长吗?怎么弄成这样?”
我爹在一旁搓着手,脸上又是急又是愧:“郎中,您快给瞧瞧!道长是为了救我家丫头才……”
王郎中定了定神,走上前来。他先翻了翻道长的眼皮,又摸了摸脉,眉头越皱越紧。等到我解开新包扎的布带,让他看那伤口时,他倒抽一口凉气,连连摇头。
“这……这伤……”他指着那模糊翻卷的皮肉,指尖都有点抖,“这不像是寻常外伤啊!这颜色,这……这边缘……恕老夫直言,这瞧着……倒像是……”
他话没说完,但脸上那惊疑恐惧的神色,谁都看得懂。他猛地收回手,像是怕沾上什么不干净的东西,又后退了两步,离床边远了些。
“王郎中,您给开个方子,无论如何……”我爹急了。
王郎中连连摆手,头摇得像拨浪鼓:“开不了,开不了!这伤,老夫从未见过!脉象也怪,忽沉忽浮,似有似无……这,这不是药石能医的症候!你们……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!”说完,竟像是逃也似的,拎起药箱就往外走,任我爹在后面怎么喊也不回头。
屋子里一下子静下来。我爹一脸灰败,我娘又开始抹眼泪。
我看着床上气息奄奄的人,又看看自己掌心被布条缠裹的烫伤,那里还在隐隐作痛。王郎中的反应,我爹娘的绝望,都像冰冷的石头,压在心里。
他不是寻常人,他的伤,自然也不是寻常伤。昨夜那一切,那些黑暗里的东西,门上的血,烫手的符,地脉的震动,还有我渡过去的、引回来的那滚烫的“炁”……都不是王郎中能明白的。
他能明白的,大概只有“救不了”这三个字。
我爹蹲在门槛上,抱着头,闷声说:“我去镇上,镇上的孙大夫,兴许……”
“爹,”我打断他,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意外,“别去了。”
我爹和我娘都抬头看我。
“王郎中说得没错,”我看着床上的人,“这伤,寻常郎中治不了。”我顿了顿,想起昨夜暗格里那两个瓷瓶,“他……他自己有药。方才喂了一些,也重新包扎了。眼下……只能看他自己了。”
我娘急了:“那怎么行!光躺着等怎么成?这伤……”
“娘!”我加重了语气,“昨夜我能活下来,是道长拼了命。现在他这样……我们除了守着,还能做什么?去镇上请郎中,一来一回大半天,郎中来了,也无非是摇头。不如省下力气,做点实际的。”
我爹看着我,眼神复杂,像是不认识我了。半晌,他重重叹了口气,没再坚持。
日头慢慢升高,透过窗纸,照在床前的地面上,拉出一道明亮的光斑。屋子里弥漫着药味、血腥味,还有一种沉重的、令人窒息的安静。只有他微弱却持续的呼吸声,提醒着时间的流逝。
我坐在那张破凳子上,没再动。眼睛看着他灰败的脸,和眉心那点固执的暗沉。
等。
除了等,别无他法。
等他自己的药起作用,等他身体里那股我无法理解的、滚烫又冰冷的力量,自己去搏杀,去修复。
或者,等那最终的结果。
日光渐渐偏移,从床前移到墙上。外头村子的声音远远传来,炊烟又起了,狗在叫,孩子在跑。那些鲜活的声音,都隔着一层无形的膜,传不进这间被药味和绝望笼罩的屋子。
不知过了多久,我娘端了碗新熬的、更稀薄的米汤进来,想让我喂他。我试了试,和之前一样,喂不进去多少,大多顺着嘴角流了出来。
就在我有些丧气地放下碗时,一直昏迷不醒的他,眼睫,忽然极其轻微地,颤动了一下。
我屏住呼吸,凑近了些。
不是错觉。
那长长的、覆着阴影的眼睫,又动了一下,然后,极其缓慢地,掀开了一条缝隙。
浑浊的,没有焦距的瞳仁,露了出来,对着头顶上方黑黢黢的房梁。
我心跳骤然漏了一拍,几乎要叫出声,又死死忍住。
他嘴唇翕动,像是在说什么,却只有气音。我凑得更近,耳朵几乎贴到他唇边。
“……水……”
还是这个字,比之前更加干渴嘶哑。
我连忙端起那碗已经温凉的米汤,用勺子舀了浅浅一点,小心地喂进他微微张开的唇缝里。
他吞咽了一下,很艰难,喉咙里发出“咕噜”一声轻响。然后,又咽了一下。
喂了小半碗,他像是耗尽了力气,眼皮重新沉重地合拢,又陷入了昏睡。
但这一次,昏睡中的他,眉头似乎舒展了那么一丝丝。虽然依旧苍白,虽然眉心那点暗沉依旧醒目,但那张脸上,仿佛有了一点极淡极淡的、属于活人的生气,悄悄渗了出来。
我轻轻放下碗,坐回凳子上,背挺得笔直。
天光依旧从窗外照进来,空气中的浮尘还在慢悠悠地飘。
等。
继续等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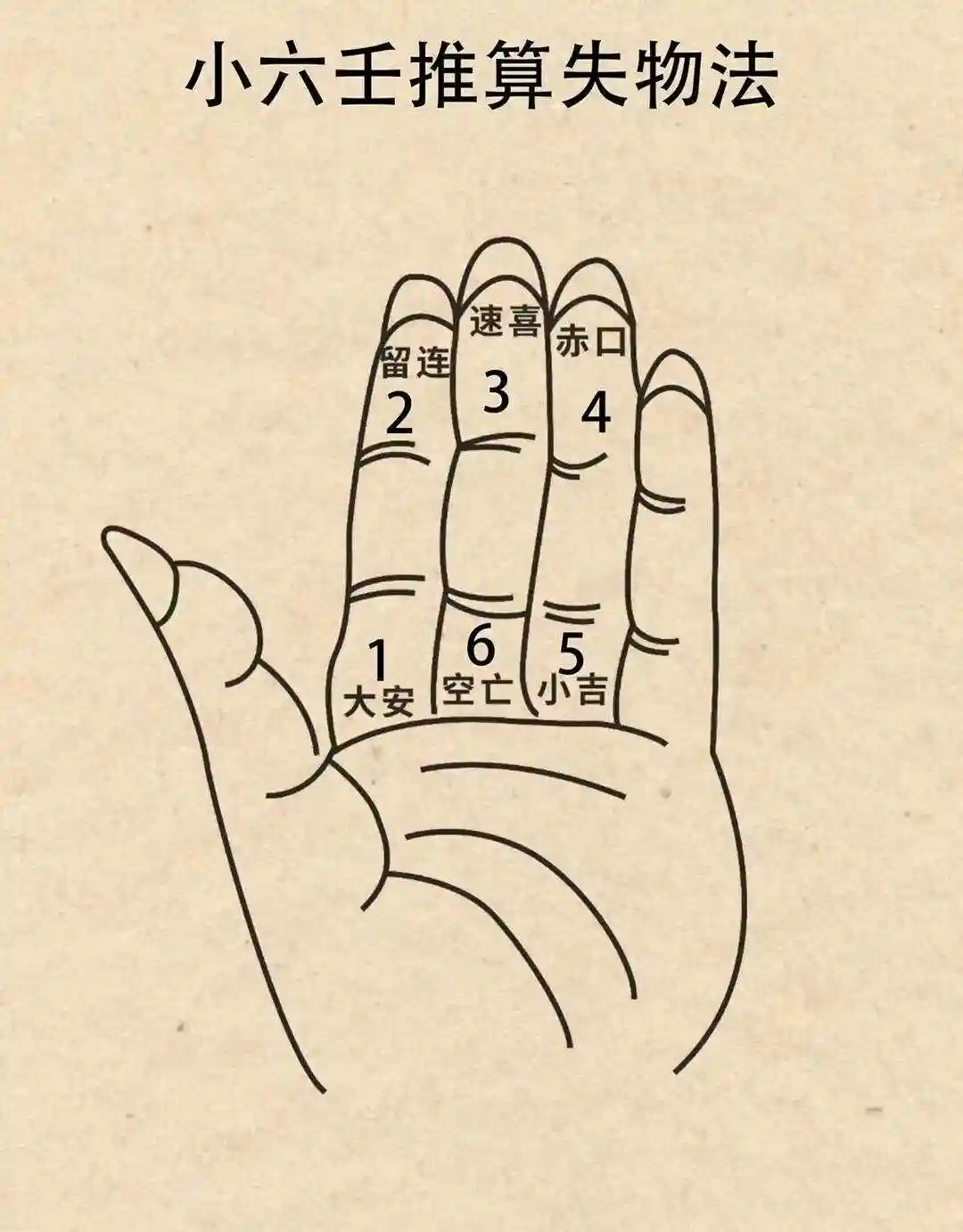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