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天傍晚,灶膛里的火映得我半边脸发烫。我守着药罐,看着罐口冒出的白汽,心思却不在上头。外头天阴得厉害,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,像是又要落雪。风不大,但吹过屋檐时,总带着一种呜呜的声响,听着心里发空。
我娘端着簸箕从堂屋出来,探头往我睡的那屋瞧了一眼,压低声音:“还是那样?”
“嗯。”我应了一声,没多说。
他还是老样子。大部分时间昏睡,偶尔会醒片刻,能喝进去些水或者极稀的米汤,喂他白色瓷瓶里的药丸,也能勉强吞咽。腰间的伤口,我每天按他醒来时那一点短暂的清醒里含混的指示,用红瓶里所剩无几的药粉清理、更换布条。伤口没有继续恶化,那些可怕的暗红色似乎淡了一点点,但愈合得极慢,慢得几乎看不出来。他的脸色依旧白得吓人,但不再是那种死人般的灰败,只是虚弱,一种深不见底的、仿佛被掏空了一切的虚弱。
最让人不安的,是他眉心那点暗沉。非但没有随着他略微好转的气色而减退,反而像是更凝实了些,颜色也更深了,青黑青黑的,嵌在苍白的皮肤上,格外扎眼。有时我盯着看久了,会觉得那一点颜色在微微蠕动,像活物一样。但眨眨眼,又觉得是光线和眼花的错觉。
他醒着的时候很少说话,眼睛总是半睁半闭,望着虚空某处,没什么焦距。偶尔目光扫过我,也是淡淡的,空茫茫的,像是在看一件无关紧要的物件。那种感觉很奇怪,好像经过那一夜,我们之间本该有什么不同了,可实际上,却比之前更加疏离。他像一座沉默的、正在缓慢风化的石碑,而我,只是碰巧路过的、沾了点碑上灰尘的人。
只有一次,大概是他醒着时比较清醒的一刻,他看着我给他换药时,缠着布条的左手,忽然极低地开口:“手……还疼么?”
我愣了一下,才反应过来他问的是我被三角符烫伤的掌心。“不碍事了。”我说,下意识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。其实还有些红肿,水泡破了的地方结了薄薄的痂,一动还是会疼。但比起他身上的伤,这实在不算什么。
他听了,没再说什么,又合上了眼。
药罐“咕嘟咕嘟”地响,水汽氤氲。我正要去拿布垫着端下来,堂屋那边忽然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动静。是我爹和我娘压低了嗓门的争执声,语气很急,还夹杂着推搡什么的声音。
我心头一跳,放下布垫,快步走过去。
刚到堂屋门口,就见我爹手里抓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柴刀,脸涨得通红,正想往外冲。我娘死死拽着他的胳膊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,又急又怕。
“你这是要干啥呀!疯了吗!”我娘带着哭腔,“那是道长!是为了救咱家丫头才……”
“我知道!”我爹低吼一声,脖子上青筋都暴起来了,“可你看看村里现在都传成什么样了!说咱家招了邪祟,说他……说他是用了什么邪法才活过来的!今儿后晌,老赵头家的孙子从咱家门口过,回去就发起高烧,嘴里胡说八道!他娘堵着门骂了半晌,你聋了没听见?!”
我娘一滞,拽着的手松了点劲,眼泪掉了下来:“那……那也不能……”
“不能怎样?!”我爹眼睛也红了,既有愤怒,也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惶恐,“再让他在家里待下去,咱们家在村里还怎么活?丫头以后还怎么嫁人?!你是要看着咱家被唾沫星子淹死,被当成瘟神躲着吗?”
他说着,又要往外挣。
“爹!”我一步跨进堂屋,挡在了门口。
我爹看见我,动作顿住了,但抓着柴刀的手背指节依旧绷得发白。
“你要做什么?”我看着他的眼睛,声音很平,却带着我自己都没料到的冷硬。
“我……”我爹避开我的目光,声音低了下去,却依旧固执,“我去道观。把他……把他东西收拾收拾,送回去。他……他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。”
“送回去?”我问,“送回那个破观?他躺在那儿,谁来管?谁来换药?谁给他水喝?”
“那是他的地方!”我爹猛地抬头,眼圈也是红的,“他是道士!他自有他的办法!咱们……咱们是寻常人家,招惹不起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!现在外头都传疯了,说咱家不干净,说丫头被他……”他后面的话没说出来,但意思谁都懂。
“我不管外头怎么说。”我看着他的柴刀,又看看我娘惊慌失措的脸,“我只知道,他为了救我,差点把命搭上。现在他还没好利索,咱们不能就这么把他扔出去。”
“可咱家……”我爹又急又气,“咱家担不起这个名声!你是个姑娘家,你以后……”
“我以后怎么样,不用别人说。”我打断他,心里那股冷硬的东西越来越清晰,“他救了我的命。这就是天大的道理。谁要嚼舌根,让他们嚼去。谁要赶他走,除非先从我身上过去。”
我爹瞪着我,像是不认识我了。手里的柴刀,“哐当”一声掉在地上。他脸上的愤怒慢慢褪去,变成一种深深的、无力的颓唐。他蹲下身,抱着头,肩膀垮了下去。
我娘看看我,又看看我爹,捂着嘴,无声地流泪。
屋子里一片死寂。只有外头呜呜的风声,一阵紧过一阵。
我弯腰,捡起那把柴刀。刀身冰凉,锈迹斑斑,没什么分量。我把它放到墙角,没再看我爹娘,转身回了灶间。
药罐里的水快熬干了,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。我把它端下来,倒出黑褐色的药汁,晾在一边。
等我端着药碗进屋时,他已经醒了。
靠坐在床头,背后垫着我娘找出来的旧枕头。眼睛望着小窗外阴沉沉的天色,侧脸的线条在昏暗的光线下,显得格外瘦削冷硬。
我走过去,把药碗递给他。
他没接,也没看药碗,目光依旧落在窗外,忽然开口,声音依旧沙哑,却带着一丝奇异的了然:“你爹……要赶我走?”
我手一抖,药汁差点洒出来。
他怎么知道?刚才堂屋的争执,声音不大,他又昏昏沉沉的……
“没有。”我把药碗塞进他手里,指尖触到他冰凉的皮肤,“先把药喝了。”
他垂下眼,看着碗里黑黢黢的药汁,没再追问。沉默地端起碗,慢慢地,一口一口,把药喝完了。眉头都没皱一下,仿佛喝的是水。
我把空碗接过来,放在一旁的小凳上。屋里又静下来。窗外的天色更暗了,风刮得窗纸哗啦啦响。
“明天,”他忽然说,声音很轻,却异常清晰,“我要回道观。”
我心里一沉,猛地抬头看他。
他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有眉心那点青黑,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下,幽幽地亮着,像某种不祥的印记。
“你的伤还没好。”我听见自己干巴巴地说。
“死不了。”他淡淡道,语气里听不出情绪,“在这里,对你们家不好。”
果然,他都听到了,或者……他早就料到了。
“我不怕。”我说,声音有点急。
他这才转过脸,正眼看我。那双眼睛很深,像两口古井,映着窗外最后一点天光,里面没有责备,没有感激,也没有我之前隐约期待的任何温度,只有一片近乎漠然的平静。
“我怕。”他说,一字一顿,清晰得残忍,“因果太重,你承不起。”
我张了张嘴,却发不出声音。一股冰冷的、尖锐的东西,从心底猛地扎上来,刺得我五脏六腑都疼。不是因为他的话,而是因为他说话时的神情。那么平静,那么疏离,仿佛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、也与我无关的事实。
他没再看我,重新转向窗外。“明天一早。”他重复了一遍,像是最后的决定,然后闭上了眼睛,不再说话。
我站在原地,看着他又恢复成那副疏离的、石刻般的模样,掌心烫伤的地方,忽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。窗外的风声更紧了,呜呜咽咽,像是无数细小的鬼魂,贴着墙根哭泣。
我慢慢转过身,走出了屋子。
堂屋里,我爹还蹲在墙角,我娘坐在凳子上抹眼泪。见我出来,他们都抬头看我,眼神复杂。
我没说话,径直走到灶台边,继续做晚饭。
锅里的水烧开了,咕嘟咕嘟地冒着泡。
明天。他说明天要走。
因果太重,我承不起。
我往锅里下了米,拿起勺子,慢慢地搅动。
滚烫的蒸汽扑在脸上,湿漉漉的,分不清是水汽,还是别的什么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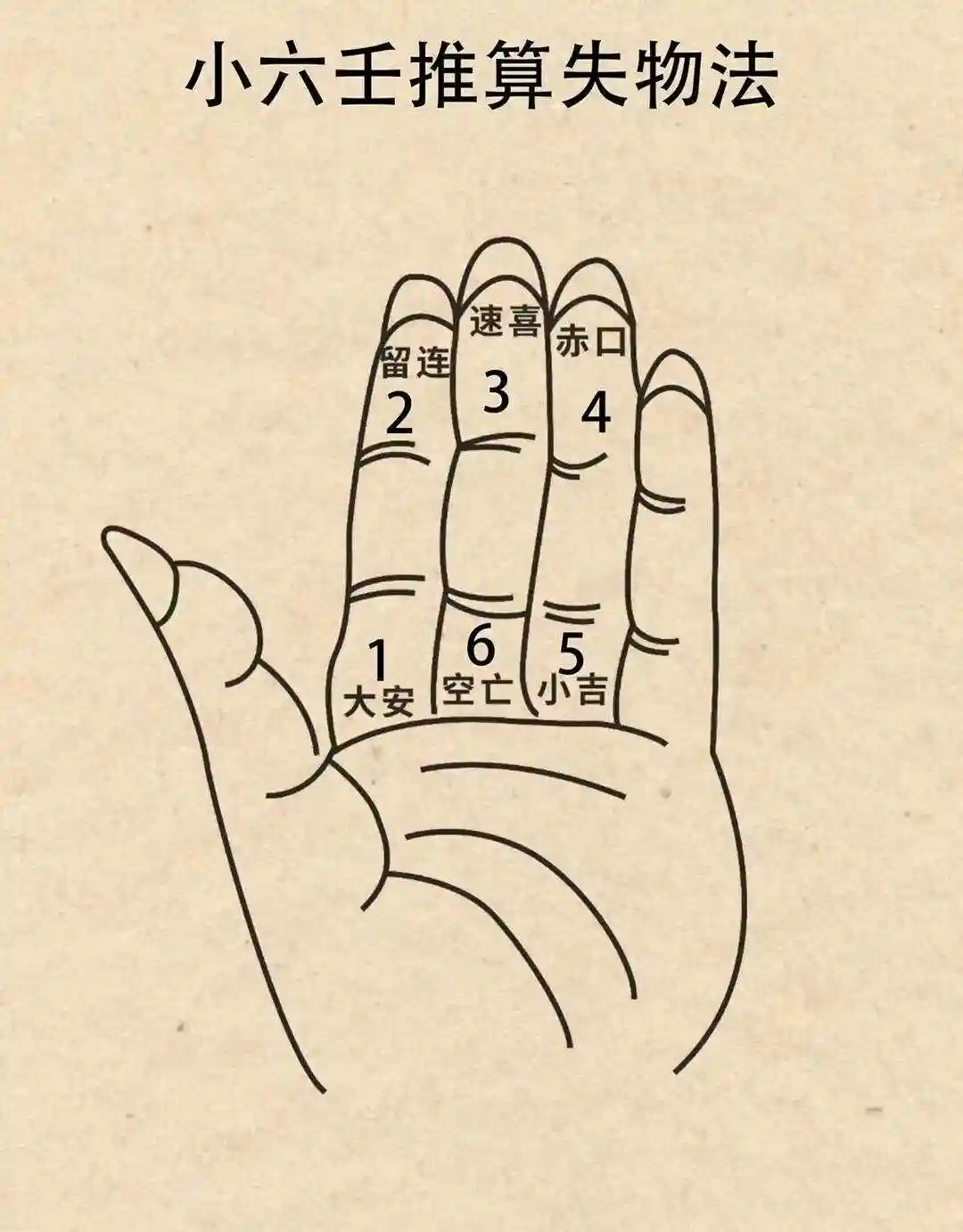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