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还没亮透,那种青灰色的、带着寒气的光,刚刚能让人看清屋里的轮廓。他就已经穿戴整齐,坐在我那张小床的床沿上了。
还是那身玄青道袍,已经洗过——是我娘昨天傍晚咬着牙,用皂角狠狠搓了,晾在灶膛边烘了大半夜。血污是洗掉了,布料却显得更加陈旧黯淡,皱巴巴的,像是缩了水,空落落地挂在他身上,越发衬得他形销骨立。腰间的伤口处,鼓鼓囊囊地缠着我撕的我爹那件旧褂子改的布条,外面又罩上了袍子,倒不太看得出来。
他脸色依旧苍白,但不再是那种虚浮的死白,而是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青气,尤其是眼圈周围,阴影很重。眉心那点暗沉,在晨光里,颜色反倒浅了些,成了更深的青灰色,不再那么咄咄逼人,却像一块洗不掉的胎记,牢牢嵌在那里。
他坐在那儿,背挺得笔直,双手虚虚地搭在膝盖上,眼睛望着对面墙壁上的一块水渍斑痕,一动不动,像一尊提前摆好了姿势、等着被抬走的泥塑。
我端着碗刚熬好的、滚烫的米粥进来时,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。粥熬得很稠,面上凝着一层薄薄的米油。我把碗轻轻放在他旁边的小凳上,热气袅袅升起,隔在我们中间。
“吃点东西再走。”我说,声音在寂静的晨光里显得有些干涩。
他眼珠极慢地转动了一下,视线从墙上的水渍移到那碗粥上,停留片刻,又移开,落回虚空。没点头,也没摇头。
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,看他没有动的意思,只好又说:“粥烫,凉凉再喝。”
他还是没反应。
屋子里静得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。堂屋那边传来我爹刻意压低的咳嗽声,和我娘窸窸窣窣收拾东西的动静,都小心翼翼的,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又隐隐不安的拘谨。
我转身想出去,把这点最后的、尴尬的独处时间留给他。刚迈开脚,身后传来碗沿和凳子轻微的磕碰声。
我停住,回头。
他端起了那碗粥,动作很慢,手指修长却没什么血色,稳稳地托着碗底。他没用我放在旁边的勺子,只是将碗凑到唇边,微微仰头,小口小口地,喝着滚烫的米粥。热气熏着他的脸,苍白的皮肤似乎有了一点点极淡的红晕,但很快又褪去。
他喝得很安静,很快。一碗粥见了底,碗壁上挂着粘稠的米浆。他把空碗放回凳子上,碗底和木头接触,发出轻微的一声“嗒”。
然后,他撑着床沿,慢慢地站了起来。动作有些滞涩,腰似乎不易察觉地弯了一下,又立刻挺直了。他站在那里,目光扫过这间狭窄的、属于我的屋子,扫过简陋的桌椅,糊着旧年窗纸的小窗,最后,落在我脸上。
那眼神依旧没什么温度,像清晨覆了霜的瓦片,清冷冷的。但似乎,又和昨天那种完全的漠然不同,里面多了点别的什么,很浅,一晃而过,快得抓不住。
“走吧。”他说,声音平稳,听不出虚弱,也听不出情绪。
他自己朝门口走去,步子迈得不大,却还算稳当。只是袍子下摆随着他的动作,轻轻晃动,显得里面那具身体格外空荡。
我跟在他身后半步远的地方。堂屋里,我爹和我娘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。我爹手里提着一个粗布包袱,里面是给他准备的几个杂面馍馍,还有一小包粗盐。我娘眼睛红红的,欲言又止。
“道长,”我爹把包袱递过去,声音有些发紧,“这点……路上垫垫肚子。家里……也没什么好东西。这次……实在是……”
他接过包袱,很轻,没看里面是什么,只微微颔首。“多谢。”两个字,客气而疏远。
我娘嘴唇动了动,最终只说了句:“道长……保重身体。”
他又点了点头,没再说话,径直走向门口,拉开了那扇掉漆的木门。
清冽的、带着霜寒的空气猛地灌了进来。天光比屋里亮堂多了,青白色,照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泥地,和篱笆上枯萎的藤蔓。村子里静悄悄的,大多数人家还没起,只有几缕炊烟,有气无力地升起来。
他跨出门槛,站定,似乎在适应外面的光线和空气,也或许是……在等什么。
我爹和我娘跟到门口,停住了,没有再往外送的意思。气氛有些凝滞。
我看着他的背影,那洗得发白的道袍,那挺直却单薄的肩背,还有袍子下隐隐透出的、腰间布条缠绕的轮廓。心里那点冰冷的、尖锐的东西,又拱动了一下。
我往前走了两步,越过我爹娘,走到他身边。
他侧过头,看了我一眼。
“我送你。”我说,声音不大,但很清晰。
我爹在我身后“哎”了一声,像是想说什么,又咽了回去。
他看着我,晨光落在他没什么表情的脸上,那双深井似的眼睛里,有什么东西极快地闪了一下,快得像是我的错觉。然后,他转回头,望着村尾的方向,淡淡地说:“随你。”
他没等我,自己迈开了步子。我落后他一步,跟着。
村子里的土路空荡荡的,只有早起觅食的麻雀在路边蹦跳。偶尔有哪家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探出个脑袋,看见我们,又像受惊似的猛地缩回去,“砰”地关上门。那种躲避和窥探,无声无息,却比昨日的指指点点更让人难受。
他走得不快,但很稳,一步一步,朝着村尾那座孤零零的破旧道观。袍角偶尔扫过路边的枯草,发出沙沙的轻响。清晨的寒气很重,他呼出的气息凝成淡淡的白雾,很快又散在空气里。
我们一路无话。
离道观越来越近,那歪斜的屋檐和褪色的墙壁在晨雾中渐渐清晰。观门紧闭着,门板上我涂抹的血痕早已干透发黑,成了一道狰狞的污迹,旁边还有昨夜抓挠撞击留下的深深浅浅的痕迹,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。
他在观门前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。
我也停下,看着他。
他没回头,只是望着那扇门,望了很久。久到我都觉得那股清晨的寒气要把人冻僵了。
然后,他抬起手,不是去推门,而是伸进洗得发白的道袍袖子里,慢慢地,摸索着,掏出了一样东西。
是一个小小的、深紫色的旧布袋。
和之前那个装药和符的袋子几乎一模一样,只是颜色似乎更沉些,布料也显得更老旧,边角磨损得厉害。系口的绳子也不是同色的细绳,而是一根看起来平平无奇、有些发黑的麻绳。
他把这个旧布袋托在掌心,递向我。
我愣住了,看着他掌心那个小小的布袋,又抬头看他。
他还是没有回头,侧脸在晨光里线条冷硬,声音比这清晨的空气更淡,没什么起伏,却一字一字,清晰地敲进我耳朵里:
“上次那个,沾了血,废了。”
“这个,你拿着。”
“若再闻到不该闻的味道,听到不该听的声音,或是……眉心发烫,心里发慌,就把它打开。”
“记住,不到万不得已,不要开。”
说完,他手又往前送了送,那旧布袋几乎触到我的衣襟。
我迟疑着,伸手接过。布袋很轻,几乎没什么分量,捏在手里,布料粗砺,带着他袖子里一点残余的、冷冷的体温,还有一种极淡极淡的、几乎闻不到的陈旧香火气。
“这里面……”我下意识想问。
“别问。”他打断我,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极细微的波动,像是疲惫,又像是别的什么,“拿着便是。”
他收回手,重新笼回袖子里,依旧背对着我。
“回去吧。”他说,顿了顿,又补了一句,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,“……昨夜多谢。”
说完,他不再停留,迈步上前,推开了那扇布满污迹和伤痕的观门。
“吱呀——”
门轴发出干涩刺耳的摩擦声。门内是浓重的、比外面更阴冷的黑暗,将他玄青色的身影一点点吞没。他没有回头,也没有再停顿,径直走了进去,反手带上了门。
“咔哒。”
门闩落下的声音,轻微,却异常清晰,像是一把锁,轻轻合拢。
我站在原地,手里攥着那个小小的、冰凉的旧布袋,看着眼前紧闭的、沉默的观门。晨光完全亮了起来,驱散了薄雾,照亮了门板上干涸的血痕和抓挠的印记,也照亮了门槛内缘那几点洗不掉的、深褐色的血迹。
村子里的人声渐渐多了起来,狗叫,鸡鸣,孩子哭,妇人唤。
炊烟笔直地升上湛蓝的天空。
一切仿佛都回到了正轨。
只有我手里这个旧布袋,沉甸甸地压着,提醒着我昨夜那场逃亡,那滚烫的唇,冰冷的血,门外的抓挠,观内的鬼影,还有他最后那句轻不可闻的“多谢”。
我站了很久,直到手脚都冻得有些麻木,才慢慢转过身,沿着来路往回走。
走了几步,我忍不住回头。
道观静静地矗立在村尾的晨光里,破败,沉默,门扉紧闭。
像一座坟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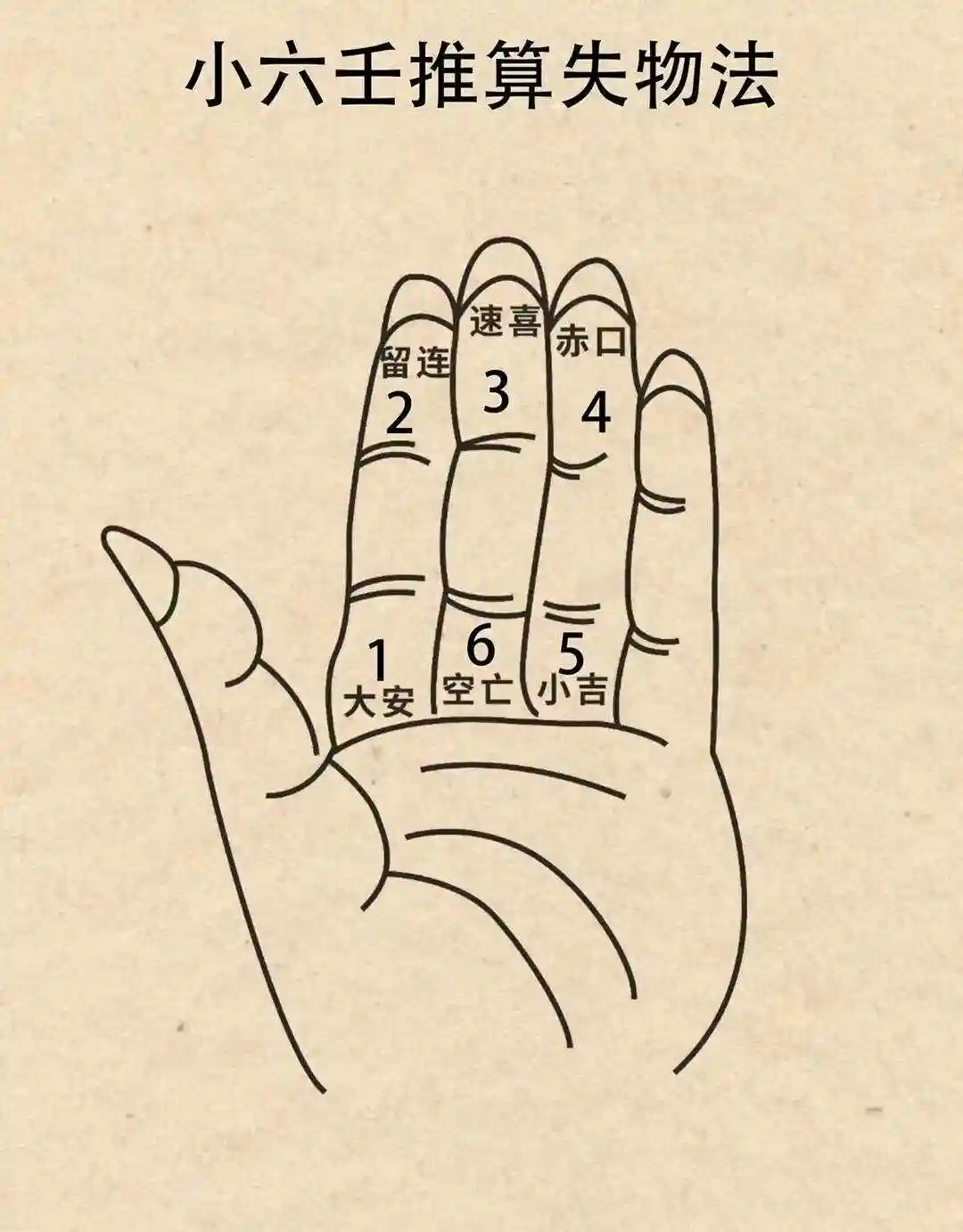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