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日子,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,硬生生掰回了原先的轨道,却又处处透着说不出的别扭。
鸡照常打鸣,日头照常升起落下。我爹扛着锄头下地,我娘围着灶台转,洗衣,喂鸡,缝补那些永远补不完的破衣裳。我也一样,烧火,挑水,打扫院子,只是话变得少了,手里做着活计,眼睛却总忍不住往村尾的方向瞟。
村里人对我们家的态度,古怪地沉默着。不再像之前那样聚在一起指指点点,但路上碰见了,眼神总是飞快地移开,招呼打得含糊其辞,带着一种刻意保持的距离。连平日里常来串门、嘴巴最碎的六婶,也绕着我家门口走。仿佛我家院子外面,多了一圈看不见的、不干净的篱笆。
我爹更沉默了,从田里回来,常常蹲在门槛上,一袋接一袋地抽旱烟,眉头锁得死紧。我娘背地里叹气抹眼泪的次数越来越多,有时看着我,嘴唇动了动,最终却什么也没说。
我知道他们在怕什么,在烦什么。那道长走了,可他留下的影子,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传闻,却像潮湿雨季里墙根下的苔藓,悄无声息地长满了我们家的屋檐。
只有我自己知道,有些东西,不一样了。
我开始怕黑。
不是小孩子那种怕鬼怕怪的怕,而是一种更细密、更无孔不入的惊悸。太阳一落山,心里就莫名发慌。屋子里必须点着灯,油灯昏黄的光晕只能照亮一小片,角落里的黑暗便显得格外浓重,仿佛藏着什么。窗外的风声,夜虫的鸣叫,甚至远处谁家狗的吠声,都能让我心头猛地一跳,竖起耳朵听半天。
那若有若无的檀香味,果然又回来了。不常出现,但总是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——比如傍晚打水,井口幽深的水面倒映着天光时;比如深夜醒来,屋里一片死寂时——丝丝缕缕地钻进鼻子,清冷干净,却让我脊背发凉。
有一次,我在灶膛前添柴,火光明明灭灭。我娘在里屋喊我拿东西,我应了一声起身,眼角余光似乎瞥见灶膛深处,那跳跃的火苗阴影里,有什么东西极快地扭曲了一下,像一张模糊的人脸,对着我咧了咧嘴。我吓得手里的火钳“当啷”掉在地上,再定睛看时,只有通红的木炭和正常的火焰影子。
我娘闻声出来,问我怎么了。我白着脸,摇摇头,说没事,手滑了。
她看着我,眼神里是深深的忧虑,却没多问。
我开始频繁地做噩梦。梦里没有具体的形象,只有铺天盖地的黑暗,门外密集的抓挠声,观里摇曳的绿色烛火,还有他满是血的脸,和最后那句“它们认你”。每次惊醒,都是一身冷汗,心脏狂跳,要睁着眼睛等到窗纸透出青白色的光,才能缓过气。
白天也恍惚。挑水时看着井里自己的倒影,会突然觉得陌生;洗衣服搓着搓着,会盯着水里漾开的皂角泡沫出神,好像那泡沫底下,随时会浮出别的东西。掌心里那个旧布袋,我一直贴身藏着,睡觉时也压在枕头下。布料粗砺的触感,成了唯一能让我稍稍安心一点的东西。有时半夜惊醒,我会不自觉地去摸它,感受那一点微凉和实在。
身体也起了变化。倒不是生病,就是容易累,手脚时常冰凉,尤其到了傍晚。吃饭没什么胃口,人眼看着就瘦了一圈,下巴尖了,眼窝也陷下去些。我娘变着法想给我弄点好吃的,一个鸡蛋也要省给我,可我吃了,也只是勉强下咽。
最让我不安的,是眉心。
那天早晨,对着水盆洗脸,撩起额发,我无意间瞥了一眼水面倒影。水里那张瘦削苍白的脸,眉心偏上的地方,皮肤底下,似乎……隐隐透出一点极淡的青色。很淡,像是不小心蹭上的脏污,又像是熬夜熬出来的暗沉。我吓了一跳,赶紧用手去擦,擦不掉。对着光线仔细看,又好像没有了。但自那以后,我总忍不住去摸那个位置,有时觉得平滑如常,有时又觉得指尖下,似乎真有一小块皮肤,温度比别处低那么一点点,触感也……稍稍有些不同,说不上来,就是感觉不对。
我不敢跟任何人说,包括我爹娘。说了又能怎样?请王郎中来看?他大概又会说些“邪祟入体”、“药石罔效”之类吓人的话,除了让家里更恐慌,毫无用处。
我只是更紧地攥着那个旧布袋。他说,不到万不得已,不要开。
什么是万不得已?像上次那样,差点死掉的时候吗?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捱过去,表面平静,底下却像是埋着一锅将沸未沸的水,闷得人透不过气。直到那天下午。
是个阴天,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着,空气又湿又闷。我娘让我去村东头李婶家借个鞋样子。回来时,抄了近路,经过村后那片老坟岗的边缘。平时白天我是不怕走这里的,村里人去地里干活,也常打这儿过。
可那天不知怎么,一走近那片长满荒草、歪斜着几块旧石碑的地方,我心里就莫名地咯噔一下。脚步不由自主慢了下来。
四周静悄悄的,连声虫鸣都没有。风穿过坟间枯草的缝隙,发出一种呜呜的、像是叹息的声音。空气里,那股熟悉的、清冷的檀香味,毫无预兆地浓烈起来,不是一丝一缕,而是扑面而来,呛得我呼吸一窒。
紧接着,我听见了声音。
不是风声。
是很多很多细碎的、拖沓的脚步声,从坟岗深处传来,沙沙沙,沙沙沙……像是很多人,赤着脚,在干枯的草叶和泥土上慢吞吞地行走。
我浑身的汗毛瞬间炸了起来,血液好像一下子冻住了,手脚冰凉。我想跑,可腿像灌了铅,钉在原地动弹不得。
那沙沙的脚步声越来越近,越来越清晰,仿佛就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。我能感觉到,有什么东西,带着阴冷的气息,正从背后靠近。
极度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,扼住了我的喉咙。我想尖叫,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只能死死地瞪大眼睛,看着前面小路上被风吹得摇晃的草尖。
就在那阴冷的气息几乎贴上我后颈的瞬间——
我怀里,贴着心口放着的那个旧布袋,毫无预兆地,**烫**了起来!
不是温,是滚烫!像一块烧红的炭突然掉进了衣襟!
“啊!”我短促地惊叫一声,痛得弯下腰,手下意识地捂向胸口。
指尖触到那个布袋,烫得我猛地缩回手。但也就是这滚烫触感袭来的刹那,身后那逼近的阴冷气息,像是被针扎了的气球,“嗖”地一下退了回去!
坟岗深处那沙沙的脚步声,戛然而止。
浓烈的檀香味,潮水般退去,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风依旧呜呜地吹着,卷起几片枯叶。四周只剩下荒草起伏的沙沙声,和远处隐约传来的、正常的村庄里的动静——谁家在喊孩子吃饭,声音拖得长长的。
我僵在原地,维持着弯腰捂胸的姿势,好半晌,才敢慢慢直起身。
冷汗已经浸透了里衣,粘在背上,被风一吹,冰冷刺骨。我颤抖着手,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那个旧布袋。
布袋静静地躺在我掌心,颜色依旧是深紫色,布料粗砺,看起来平平无奇。刚才那股几乎要灼伤皮肤的滚烫,已经彻底消失了,摸上去,甚至比我的体温还要凉一些。只有系口的、那根发黑的麻绳,似乎……比之前更黑了一点,像是被火微微燎过。
我紧紧攥着它,心脏还在胸腔里疯狂擂鼓,手脚软得几乎站不住。
刚才……是它?
是它在……保护我?
我慢慢转过身,望向那片荒草萋萋的坟岗。日头被厚厚的云层遮着,光线昏暗,坟包和石碑在灰色的天幕下投出沉默而怪异的影子。那里静悄悄的,什么都没有。
可我知道,刚才不是幻觉。
我低下头,看着手里这个救了我一次的旧布袋。他说,不到万不得已,不要开。
刚才,算万不得已吗?它自己……烫起来了。
那下一次呢?
我把它重新塞回怀里,贴着心口放好。那里,皮肤似乎还残留着一丝灼痛后的麻木。
我不敢再停留,几乎是踉跄着,逃离了那条小路。跑出很远,直到看见村里人家屋顶的炊烟,听见清晰的狗叫声,才敢放慢脚步,靠着路边一棵老槐树,大口大口地喘气。
傍晚回家,我娘看我脸色煞白,额发都被冷汗打湿了,吓了一跳,连声问我是不是不舒服。
我摇摇头,说走路急了,有点累。
吃饭时,我爹看我魂不守舍,碗里的饭扒拉了半天也没见少,皱着眉,瓮声瓮气地说:“多吃点,看你瘦的。”
我“嗯”了一声,强迫自己往嘴里塞了一口饭,味同嚼蜡。
晚上,我早早躺下了,却睁着眼睛,毫无睡意。窗外的风声似乎又紧了,吹得窗纸哗啦啦响。我侧躺着,手伸进枕头底下,紧紧攥着那个布袋。冰凉的布料贴在掌心,带来一点点微弱的安心感。
眉心那处,似乎又开始隐隐发烫,不是布袋那种灼痛,而是一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、阴冷的烫。
我翻了个身,脸埋进粗糙的枕头里。
夜还很长。
而那个小小的、救了我一次的旧布袋,和我眉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感觉,像两颗冰冷的石子,沉甸甸地压在心底。
我不知道,它们还会带来什么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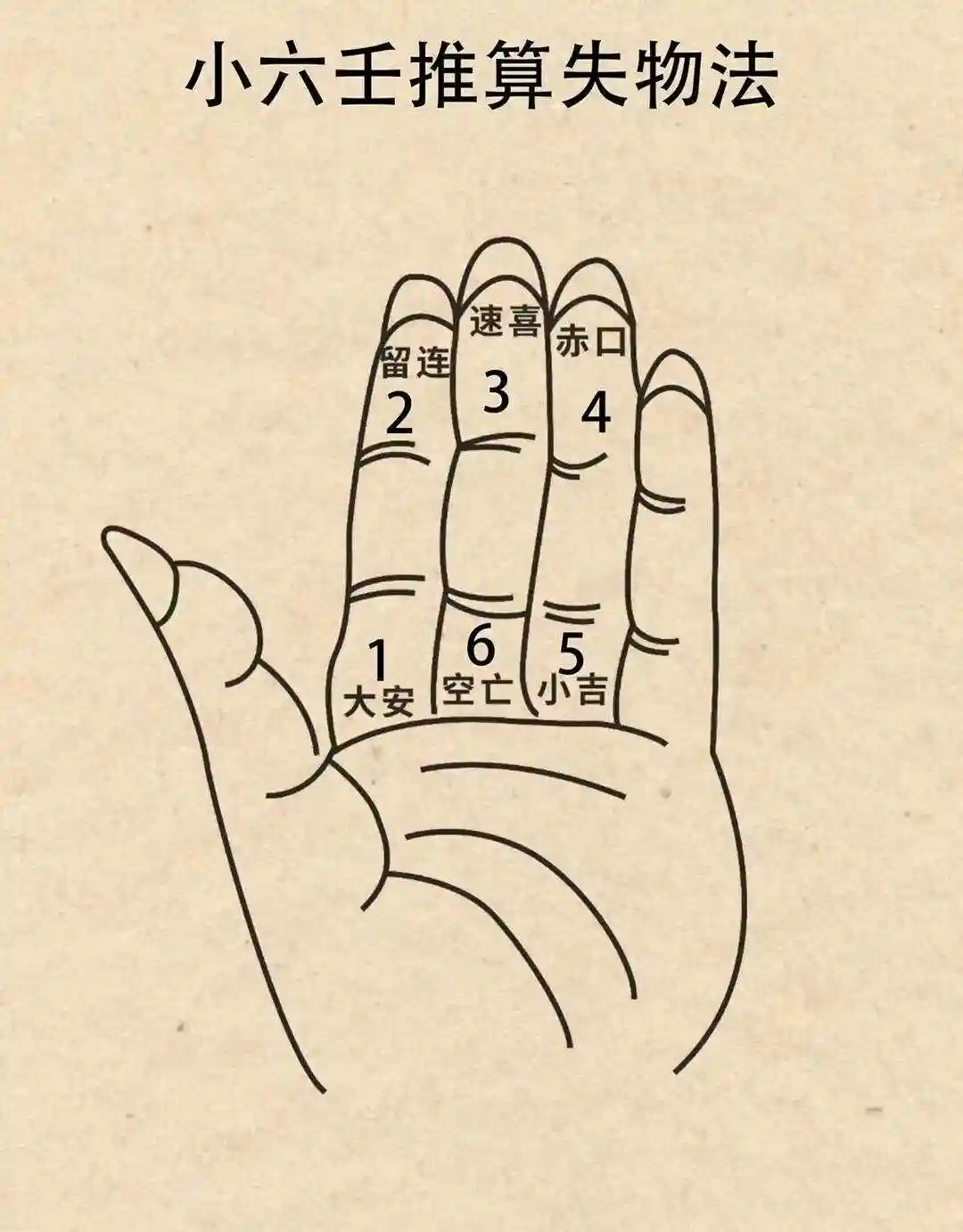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