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刚擦黑,我娘就把堂屋那盏油灯点上了。灯芯剪得短,火苗只有黄豆大,昏黄的一团,勉强照亮方寸之地,反而把四角的阴影衬得更浓。我爹蹲在门槛外头抽烟,烟锅子里的火光明明灭灭,映着他一张愁苦的脸。谁也没提白天坟岗边的事,但屋子里那股沉闷,比以往任何一天都重,压得人胸口发堵。
胡乱扒了几口饭,我就回了自己那屋。没点灯,摸黑坐在床沿上。窗户纸上糊着去年剩下的旧纸,破了几个小洞,漏进外头一点点青灰色的天光,勉强能看见屋里桌椅模糊的轮廓。我靠着冰冷的土墙,眼睛望着那片混沌的黑暗,耳朵却竖着,捕捉着外头每一点细微的声响。
风比傍晚时小了些,但没停,像生了病的人,有气无力地哼着,刮过屋檐,带起呜呜的尾音。远处谁家的狗短促地叫了两声,又没了动静。村子像是沉进了一潭粘稠的、墨黑的水里,寂静得让人心慌。
怀里那个旧布袋贴着心口,冰凉一片,毫无动静。白天在坟岗边那股灼人的滚烫,像是耗尽了它最后一点力气,此刻沉寂得如同一块普通的石头。
时间一点点熬过去。油灯的光从堂屋门缝底下漏进来一线,昏黄,微弱,摇曳不定。我爹的咳嗽声,我娘压抑的叹息,偶尔传来,又迅速被寂静吞没。
不知过了多久,我眼皮开始发沉,意识也有些模糊。就在半睡半醒之间——
“咚。”
一声闷响,从很远的地方传来,像是什么沉重的东西,砸在了地上。
我猛地惊醒,心脏骤然缩紧。
那声音……不像是村子里正常的响动。太闷,太沉,带着一种……说不出的空旷感。
我屏住呼吸,侧耳细听。
外面风声依旧,呜呜咽咽。
仿佛刚才那一声,只是我的错觉。
可心里的不安,却像滴进清水里的墨,迅速晕开,再也无法平息。我坐直了身子,手不自觉攥紧了衣襟,指尖隔着薄薄的布料,触到那个冰凉的布袋。
又过了约莫一炷香的功夫。
“咚。”
又是一声。
比刚才清晰了一点,似乎也更近了一点。依旧是那种闷闷的、沉重的撞击声,间隔均匀,不紧不慢,带着一种机械的、毫无生气的节奏。
这一次,我听得真真切切。不是幻听。
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,后背瞬间爬满冷汗。我僵硬地转过头,望向那扇对着院子的小窗。窗纸破洞外,是浓得化不开的夜黑,什么都看不见。
那“咚咚”的声音,第三次响起。
这一次,更近了。近得仿佛就在……村尾的方向。
是道观!是他那里!
这个念头像一道冰冷的闪电,劈进我混沌的脑海。是他出事了?还是……别的什么?
我“嚯”地一下站起来,腿却软得踉跄了一下,扶住冰冷的土墙才站稳。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撞击,耳朵里全是血液奔流的轰鸣声。
去?还是不去?
白天坟岗边那阴冷的气息和沙沙的脚步声,还有怀里布袋突如其来的滚烫,瞬间涌回记忆。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,死死攥住了我的喉咙。
可那“咚咚”的撞击声,还在继续。不疾不徐,一声,又一声,在死寂的夜里,敲得人头皮发麻。每一声,都像敲在我的心尖上。
我脑子里乱成一团。想起他洗得发白的道袍,想起他苍白脸上眉心那点暗沉,想起他最后递给我布袋时,那双深井般无波无澜的眼睛,和那句轻不可闻的“……昨夜多谢。”
还有那句,“因果太重,你承不起。”
我知道。我都知道。
可那“咚咚”的声音,像催命的鼓点,一下下砸过来。
我猛地吸了一口气,冰凉的空气刺得肺叶生疼。手指颤抖着,从怀里掏出那个旧布袋,死死攥在掌心。冰凉的布料硌着皮肉,带来一丝微弱的清明。
我转身,轻手轻脚地拉开房门。堂屋里的油灯还亮着,我爹娘那屋门关着,里面传来我爹粗重的鼾声。他们睡着了,或者说,他们强迫自己睡着了,不去听外面那不祥的声响。
我没惊动他们,赤着脚,悄无声息地拉开堂屋门,闪身出去,又轻轻掩上。
院子里的寒气立刻包裹上来,激得我打了个哆嗦。天上一颗星星都没有,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锅。只有远处村尾的方向,那“咚咚”的闷响,依旧固执地传来,在寂静的夜里,清晰得瘆人。
我贴着墙根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。手心紧紧攥着那个布袋,指甲几乎要掐进布料里去。心脏跳得又急又重,撞得耳膜生疼。
刚走到院门口,手还没碰到门闩——
“吱呀——”
身后我爹娘那屋的门,突然开了。
我浑身一僵,猛地回头。
昏黄的灯光从门里泻出来,照亮我娘惊慌失措的脸。她披着外衣,头发散乱,眼睛睁得老大,死死盯着我,嘴唇哆嗦着,声音压得极低,却带着尖锐的颤音:“你……你要去哪儿?!”
我张了张嘴,却发不出声音。
“回去!”我娘猛地冲过来,一把抓住我的胳膊,力气大得惊人,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,“你疯了是不是?你听听外头是什么动静!你还敢往外跑?!回去!给我回屋去!”
她声音里带着哭腔,是真正的恐惧,不是为了面子,不是为了名声,是母亲护着崽子、面对不可知危险时最本能的恐惧。
“娘……”我喉咙干涩,“我……”
“别叫我娘!”她几乎是低吼出来,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,混着油灯昏黄的光,在她脸上留下凌乱的光痕,“你是不是要气死我?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道士?他……他不是咱们能招惹的人!他那里……他那里现在……”她没说完,但眼神里的惊恐说明了一切。她也听见了那“咚咚”声,她知道那不寻常。
她死死拽着我,要把我拖回屋里。我爹也被惊动了,趿拉着鞋出来,看到我们拉扯,脸色铁青,低喝道:“闹什么!都给我进去!”
就在这时——
“咚!!!”
一声比之前所有声响都更加沉闷、更加巨大的撞击声,猛地传来!那声音仿佛就炸在耳边,连脚下地面都似乎随之震颤了一下!
紧接着,是“哗啦”一声巨响,像是木石结构的东西,被硬生生撞碎、垮塌的声音!
声音传来的方向,正是村尾道观!
我娘拽着我的手猛地一松,脸上血色尽褪,踉跄着后退一步,撞在门框上。我爹也骇然望向村尾方向,张着嘴,说不出话。
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瞬。
然后,一片死寂。
那持续了许久的“咚咚”声,停了。
令人心悸的、绝对的寂静,重新笼罩下来,比之前那催命般的敲击声,更加可怕。
我娘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,顺着门框滑坐到地上,捂着脸,压抑地啜泣起来。我爹僵在原地,脸色灰败。
我站在原地,手心里那个旧布袋,依旧冰凉。
可我知道,有什么东西,已经发生了。
刚才那最后一声巨响……是观门?还是别的什么?
他……
我不敢想下去。
夜风吹过,卷起地上的尘土和枯叶,打着旋儿,发出“沙沙”的轻响。远处,村尾的方向,一片沉沉的黑暗,再无半点声息。
我慢慢转过身,背对着瘫软啜泣的娘亲和呆立无言的爹,望向那吞噬了一切的黑暗深处。掌心,那个小小的布袋,沉甸甸地坠着。
寂静,无边无际的寂静,像一张湿透的厚牛皮,严严实实地蒙了下来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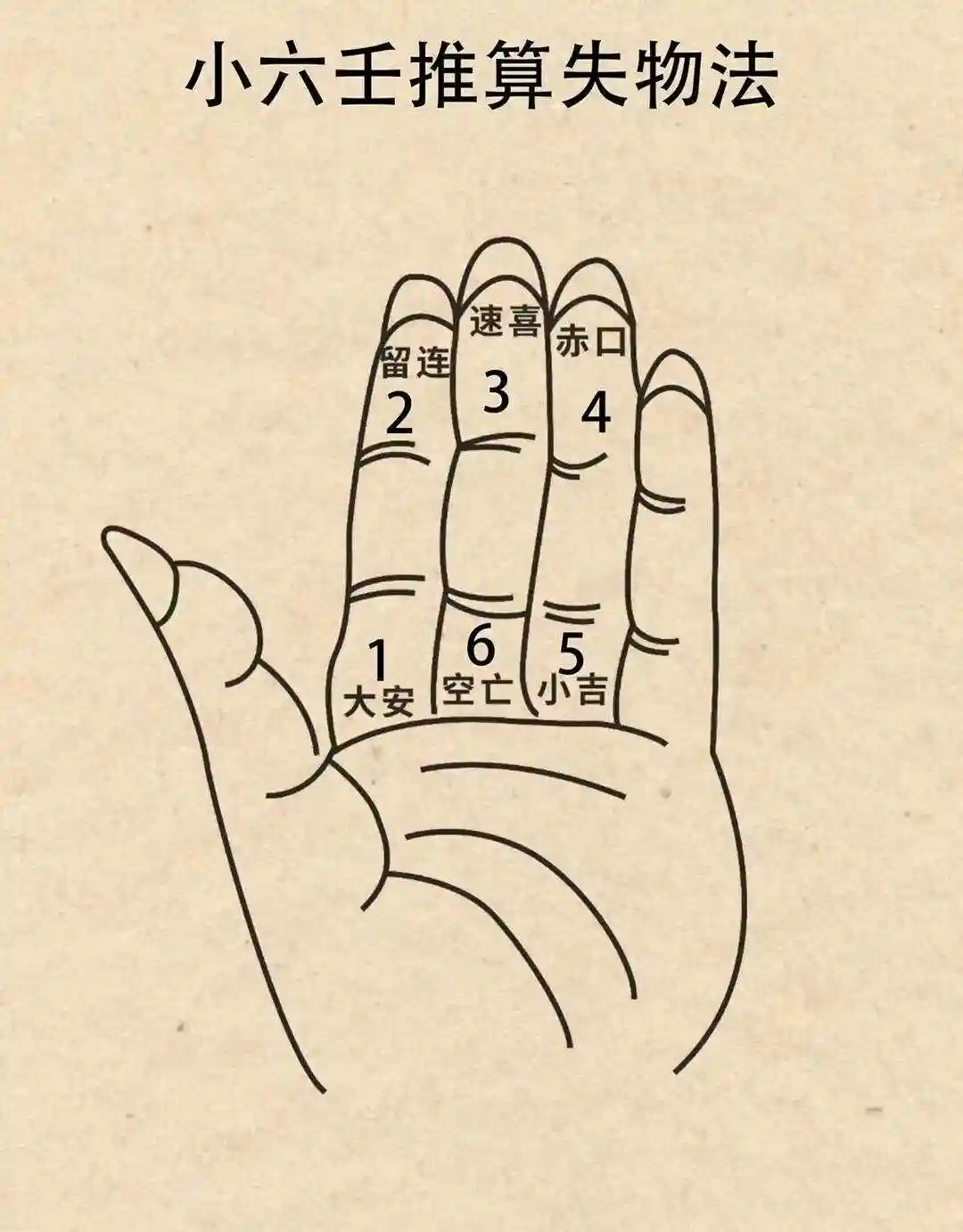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