黑暗像一口倒扣的锅,严丝合缝。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说不上来是哪里,就是感觉不同。刚才那种浸到骨髓里、让人想放弃挣扎的阴冷,退潮般淡了些。空气里那无处不在的、细细碎碎的窸窣声,也消失了,只剩下一种空旷的、令人心慌的死寂。
掌心的灼痛一阵阵传来,提醒我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嘴唇上也还残留着那种冰冷的粗糙感,和之后突兀的、烙铁般的滚烫。我靠在墙上,浑身虚脱,耳朵里还在嗡嗡响,眼前仿佛还晃动着那些炸开的猩红与金白的光斑。
他的呼吸声就在旁边,依然很轻,但节奏稳了。不再是那种随时会断气的、拉风箱似的杂音,而是均匀的、绵长的吐纳。在这绝对的黑暗和寂静里,这声音清晰得有点……不真实。
我慢慢地,极其缓慢地伸出手,在黑暗里摸索。指尖先是碰到冰冷粗糙的砖地,然后是他的道袍下摆,湿冷黏腻的感觉还在。再往上,是他的手臂,隔着浸血的布料,能感觉到底下肌肉的轮廓,僵硬,但似乎……不再那么冰冷彻骨了。
我的手停在那里,不敢再动。
时间一点点流走,或许很久,或许只是一会儿。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,对时间的感知完全错乱了。我全身的酸痛在冰冷的地面刺激下愈发鲜明,眼皮沉得像坠了铅,但我不敢睡。黑暗本身就是最大的威胁,谁知道那些退去的东西会不会卷土重来?
就在意识又开始模糊,身体因为寒冷和疲惫而微微打颤的时候,我听到了一个声音。
不是外面的,也不是观里那些鬼祟的动静。
是他。
一声极低、极压抑的抽气,带着刚醒来的滞涩和痛楚,然后是一阵猛烈的呛咳。
我猛地一激灵,彻底清醒了,心脏狂跳起来,摸索着朝他那边凑近了些。
咳嗽声持续了几声,渐渐平复下去。然后是衣物摩擦的窸窣声,他似乎想动,又无力地停了下来。
“……水。”沙哑得几乎破碎的音节,从黑暗中传来。
水?我愣了一下,才想起之前那个陶罐。我赶紧在记忆里确认了一下方位,手脚并用地爬过去,指尖触到冰凉的陶罐壁。拿起来晃了晃,里面还有一点点,大概只剩一口了。
我捧着陶罐,又爬回他身边。黑暗中看不清,我试探着伸出手,摸到了他的肩膀,顺着往上,碰到他的脸颊。指尖传来的温度让我心头一颤——不再是那种死人般的冰冷,虽然依旧偏低,但有了活人的温热。
我小心地托起他的头,把陶罐凑到他唇边。这一次,他配合地微微张开嘴,就着我的手,将罐里最后一点水咽了下去。喉结滚动,发出轻微的“咕咚”声。
喝完了水,他没立刻说话,只是喘息了片刻,那气息依旧虚弱,却有了根。
“你……”他又开口,声音比刚才清晰了一点点,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沙砾里磨出来的,“做了什么?”
我浑身一僵,托着他头的手差点松开。脸上猛地烧了起来,幸好黑暗掩盖了一切。喉咙发干,我张了张嘴,却发不出声音。难道要我说,我……我又……
“不是问那个。”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窘迫,或者根本没力气纠结那个,喘了口气,声音低了下去,带着一种深深的疲惫和……疑惑,“刚才……地脉……震了一下。你身上……有我的‘炁’在乱走。还有……”他顿了顿,似乎在感应什么,“观里的‘脏东西’,被惊退了。”
他的“炁”?是指……那股滚烫的气流?地脉震动?是我和他……那时引起的?
我脑子里乱成一团,只能僵硬地保持着托着他头的姿势,一动不动。
他也没再追问,仿佛光是说这几句话就耗尽了力气。沉默再次降临,但这一次,沉默里少了些令人窒息的绝望,多了点茫然的、劫后余生的虚浮。
又过了许久,久到我的手臂都开始发麻,他才再次开口,声音更低了,几乎像是在自言自语,又像是在问我:“现在……什么时辰了?”
我茫然地“看”向四周,一样的漆黑。“不……不知道。蜡烛,早就灭了。”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,似乎并不意外。然后,我感觉他动了一下,不是大的动作,只是头微微偏了偏,好像在黑暗中“看”向我这边。“你……把手伸过来。”
我一怔,犹豫着,缩回了托着他头的手,在衣襟上擦了擦——虽然手上依旧满是血污和尘土——然后,迟疑地朝他声音的方向伸出手去。
一只温热(比起之前,已经是温热了)而干燥的手,准确地在黑暗中握住了我的手腕。他的手指依旧没什么力气,但握得很稳。指腹带着薄茧,轻轻按在我的腕脉上。
我屏住呼吸。
他按了片刻,手指又微微移动,似乎是在探查我掌心——正是被三角符烫伤的地方。指尖触到那片火辣辣的皮肤时,我忍不住轻轻“嘶”了一声。
他动作顿住,然后极轻地叹了口气。那叹息里混着太多的东西,疲惫,了然,或许还有一丝无可奈何的认命。
“胡闹。”他吐出两个字,却没什么责怪的意思,只是陈述。然后松开了我的手。
手腕上还残留着他手指的温度和触感。我默默收回手,蜷缩起来。
“外面……”我忍不住,声音细小地问,“那些……还在吗?”
他没有立刻回答。寂静中,我仿佛能感觉到他在凝神倾听,或者用别的什么方法感知。
“在。”半晌,他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,但语气并不特别凝重,“被门上的血镇着,一时半会儿进不来。但天快亮了。”
天快亮了?我精神一振。在这绝对的黑暗里,我根本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,更别提判断天亮。
“你怎么知道?”话脱口而出,我才觉得唐突。
他又沉默了一下,才道:“地气在转。阴煞之气在退潮。”他停了一会儿,补充了一句,声音里带着一种奇异的笃定,“鸡鸣之前,会退干净。”
鸡鸣……
我们不再说话,静静地等待着。黑暗依旧,寒冷依旧,但好像没那么难熬了。他的存在本身,哪怕只是那平稳的呼吸声,就成了一根定海神针。
时间一点一滴过去。渐渐地,我感觉到,那浓稠的、有实质般的黑暗,似乎真的在变淡。不是看见了什么,而是一种感觉,仿佛墨汁里滴进了清水,虽然依旧漆黑,却不再那么密不透风。空气里的阴冷也在一点点散去,虽然还是很冷,但已是深秋清晨那种正常的寒意。
就在我感觉黑暗稀薄到某个临界点时——
遥远地,极其遥远地,从村子方向,传来了一声模糊的、微弱的“喔——喔喔——”
鸡鸣了。
几乎就在鸡鸣声响起的同一刹那,门板上那道早已干涸的血痕,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抹过,颜色骤然黯淡下去,成了普通污渍的模样。门外那片一直盘踞不散的、令人心悸的黑暗与死寂,像阳光下的霜露,悄无声息地消散了。清晨微弱的、青灰色的天光,终于艰难地透过破烂的窗纸和门缝,一丝丝地挤进了道观。
观内一点点亮了起来。先是模糊的轮廓,神像斑驳的泥塑,供桌缺角的边缘,地上散乱的蒲团,角落里堆着的杂物……然后,是他。
他就躺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,侧对着我。天光落在他脸上,惨白得吓人,眼窝深陷,嘴唇干裂灰败,下颌和颈侧沾染着已经变成黑褐色的血污。那身玄青道袍更是被血和泥污浸染得看不出原色,紧紧贴在身上,勾勒出瘦削而僵硬的线条。唯有眉心那点暗沉,在天光下显得愈发清晰,像一小块洗不掉的墨渍。
但他睁着眼睛。
那双眼睛正看着我,眸色很深,映着透进来的微光,里面没有责怪,没有愤怒,甚至没有什么明显的情绪,只有一片近乎虚无的平静,和深不见底的疲惫。
我也看着他,看着我们之间狼藉的地面,干涸发黑的血迹,散落的香烛灰,还有我手里那个空瘪的旧布袋和彻底失去光泽的三角符。
谁也没说话。
直到又一波更响亮的鸡鸣声从村中传来,伴随着几声隐约的犬吠,人世间的声音重新回到耳边。
他眼睫颤动了一下,极其缓慢地,试图撑起身体。
我下意识想过去扶,手伸到一半,又僵住了。
他试了两次,才勉强用胳膊肘支起上半身,靠在身后的墙上,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让他额头冒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,喘息也变得粗重。他闭了闭眼,再睁开时,目光扫过门板,扫过观内,最后落回我身上。
“天亮了。”他说,声音依旧沙哑,却平静地陈述着这个事实。
然后,他的视线下移,停在我紧攥着布袋和旧符的手上,停留了片刻,又移开,望向门外逐渐明亮起来的天光。
“走吧。”他吐出两个字,不知是对我说,还是对他自己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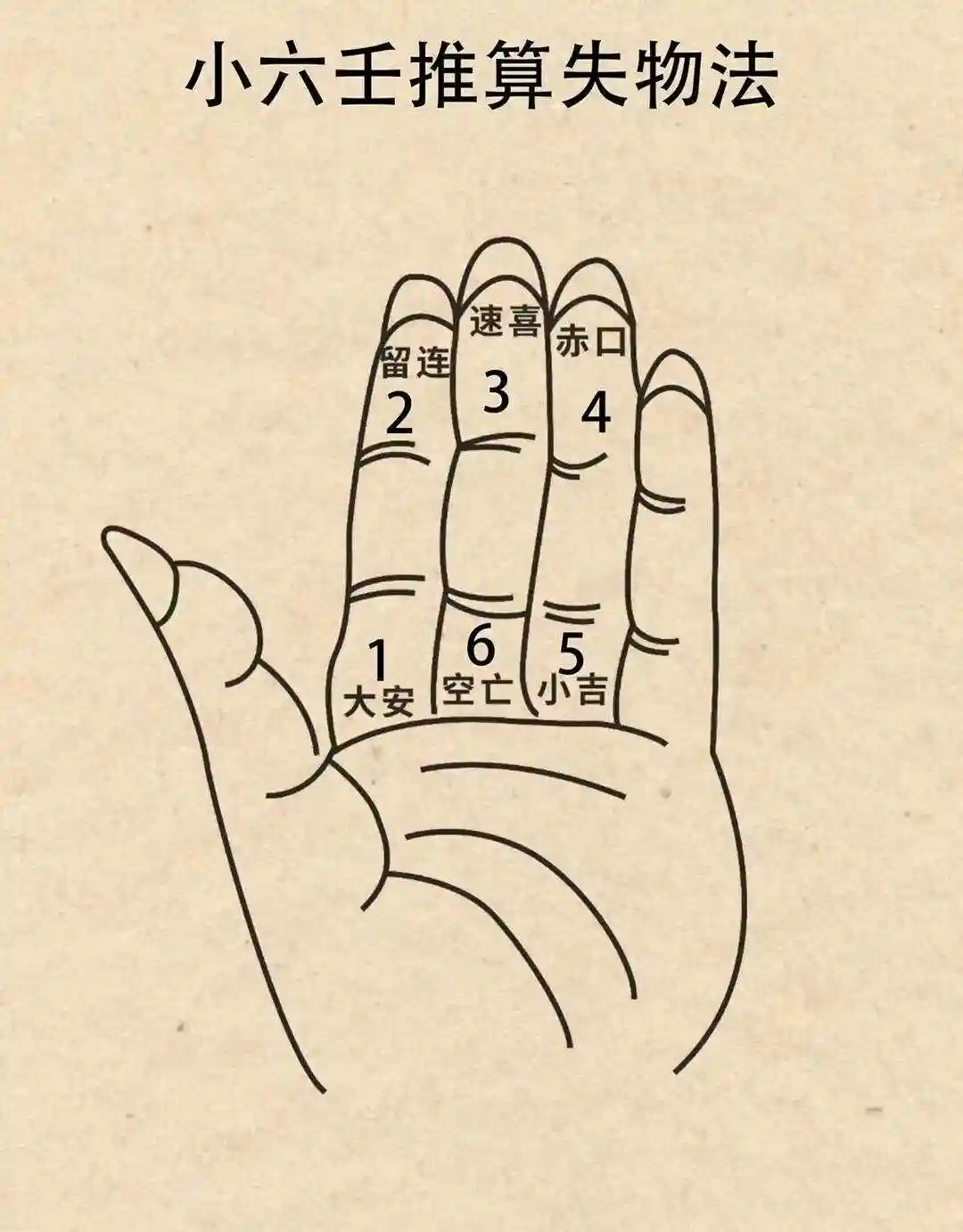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