幽绿的烛火猛地一跳,最后那点豆大的光亮,像被人掐住了脖子,挣扎着闪了两下,“噗”地一声,灭了。
黑暗,彻头彻尾的黑暗,瞬间吞噬了一切。
不是寻常的、慢慢适应了能看见轮廓的黑,而是浓稠的、厚重的、仿佛有实质的墨,劈头盖脸地砸下来,淹没了神像,淹没了供桌,淹没了我和他。眼睛完全成了摆设,耳朵里只剩下自己狂乱的心跳和粗重的喘息,还有……一种奇怪的、细微的窸窣声,从四面八方传来,像是很多脚在灰土上摩擦,又像是很多细小的嘴巴在咀嚼着什么无形的东西。
冷。那阴寒的气息没了烛火最后一点温度的对抗,变本加厉地往骨头缝里钻。我死死攥着那个空布袋和黯淡的三角符,指节硌得生疼,这是唯一能感觉到的东西,还有身下粗糙冰冷的砖地,以及……旁边他身体传来的、越来越微弱的起伏。
他还在呼吸,但轻得几乎感觉不到,每一次吐息都带着一种滞涩的、拉风箱般的杂音,间隔越来越长。
窸窣声在靠近。很慢,但确确实实,从墙角,从屋顶,从那些看不见的阴影里,朝着我们躺的地方围拢。空气里的檀香味又浓了起来,这次混着一股土腥气和……淡淡的焦糊味。
我浑身僵硬,连发抖的力气都快没了,只能睁大眼睛(尽管什么也看不见),徒劳地“瞪”着黑暗。绝望像冰冷的藤蔓,缠紧了喉咙。血干了,符废了,灯灭了。接下来是什么?被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撕碎?还是像他一样,无声无息地死在这冰冷的黑暗里?
沾了他的血……它们认我……
这句话又鬼魅般浮现在脑海。不止是血……如果……如果不止是血呢?
黑暗中,我的手颤抖着,摸索着,碰到了他的脸。冰冷,僵硬,像一块浸在寒潭里的石头。指尖划过他的下颌,触到他干裂起皮的嘴唇。
病重时那滚烫的、带着铁锈与檀香气息的触感,毫无预兆地撞进记忆。那渡过来的一口气,烧灼四肢百骸,却也硬生生把飘散的魂拽了回来。
现在呢?
现在他快死了。那口气,快散了。
一个疯狂到极点的念头,压过了所有的恐惧和羞耻,在我冻僵的脑子里噼啪炸响——如果……把那股气,还给他一点呢?如果……那不止是救命的“气”,也是某种标记,某种……联系?
窸窣声几乎到了耳边,阴冷的气息已经拂上了我的脖颈。
没有时间了。
我凭着记忆和触觉,猛地俯下身,摸索着,找到了他的嘴唇。冰冷,带着血痂的粗糙感。我笨拙地、毫无章法地贴了上去,然后,用尽仅存的力气,深吸一口气——吸进肺里的只有观内阴冷污浊的空气——再不管不顾地,朝着他嘴里渡过去。
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这根本违背常理,甚至带着亵渎。可我没办法了。我只能赌,赌那一次肌肤之亲留下的不止是麻烦,赌那口“气”里,有比血更深的印记。
第一口气渡进去,毫无反应。他依旧冰冷僵硬。
我抬起头,急促地喘息,胸腔因缺氧和恐惧而刺痛。周围的窸窣声停了,那股逼近的阴冷也似乎凝滞了一瞬,像是在观察,在疑惑。
不行吗?
绝望再次攫紧心脏。但我没有退路了。
我再次低头,贴上他的唇。这一次,我努力回想着病重时那种濒死的感觉,想着他渡气时那种灼热霸道的力量,想着他身上挥之不去的香火味……我把这些杂乱无章的意念,连同又一口微温的气息,一起用力地、缓慢地,渡了过去。
时间在黑暗中被拉长。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。
就在我几乎要脱力放弃的时候——
他的嘴唇,极其轻微地,动了一下。
不是回应,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抽搐。
但紧接着,我感觉到,我与他紧贴的唇间,传来一丝极其微弱、几乎难以察觉的暖意。不是他身体的温度,而是从更深的地方,从他喉咙深处,渗出来的一点点……热流。
那热流细若游丝,却异常灼烫,像烧红的针尖,顺着我们相贴的唇,猛地刺了回来,扎进我的舌根,瞬间冲上头顶!
“唔!”我闷哼一声,想退开,却像被无形的力量钉住了。那股灼烫的气流在我体内乱窜,所过之处,冰寒退却,却留下一种诡异的、被灼伤的麻木感。与此同时,我左手掌心一直攥着的、那张黯淡的三角符,毫无预兆地**烫**了起来!
不是温,是滚烫!像一块烧红的炭突然被塞进手里!
我痛得几乎要甩手,符纸却像粘在了掌心。那滚烫的热度顺着我的手臂急速蔓延,与我体内乱窜的、从他那里回流过来的灼热气流轰然撞在一起!
“啊——!”我再也忍不住,短促地惨叫出声,眼前虽然没有光,却猛地炸开一片刺目的、混乱的猩红与金白交织的虚影!耳朵里嗡鸣一片,仿佛有无数铜钟在颅内疯狂敲响!
就在这极致的痛苦和感官的混乱中,我感觉到,我身下的地面,不,是整个道观,极其轻微地震动了一下。
不是门外撞击的那种震动,而是更沉闷,更深沉,仿佛地底有什么东西被惊动了,翻了个身。
那几乎贴到我后背的窸窣声和阴冷气息,潮水般退去,缩回了黑暗深处,带着一种惊疑不定的仓皇。
掌心的滚烫和体内的灼流慢慢平息,变成一种虚脱的、遍布全身的酸痛。我瘫软在他身上,额头抵着他冰冷的颈侧,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汗水和不知道是泪还是别的什么,混在一起,流了满脸。手里的三角符不再滚烫,恢复了冰冷,甚至比之前更黯淡,仿佛所有的力量都在刚才那一瞬燃尽了。
黑暗中,一片死寂。
只有他胸膛的起伏,似乎……比刚才明显了一点点。虽然依旧微弱,但那种拉风箱般的滞涩杂音,减轻了。
我撑起一点身子,颤抖的手摸索着,再次探到他鼻下。
气息,依然微弱,却带上了一丝极其细微的、温热的潮意。
我瘫坐回去,背靠着冰冷的墙壁,浑身脱力,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左手掌心火辣辣地疼,不用看也知道肯定烫伤了。嘴里还残留着那股灼烫的、混合着铁锈和奇异檀香的余味。
赌对了吗?还是……引发了更糟糕的东西?
我不知道。
黑暗依旧浓重,门外的威胁并未解除,观内潜伏的影子也只是暂时退却。但就在这片绝望的漆黑和死寂里,我和他之间,似乎有某种看不见的、滚烫的线,因为刚才那孤注一掷的接触,被重新连接了起来,微弱,却顽固地搏动着。
我靠在墙上,在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寒冷中,听着他逐渐趋于平稳(虽然依旧微弱)的呼吸,第一次清晰地感觉到,那根线另一端的温度,正极其缓慢地,一丝丝地,渡过来。
很烫。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、近乎暴烈的生机,却也灼得人生疼。
就像他这个人一样。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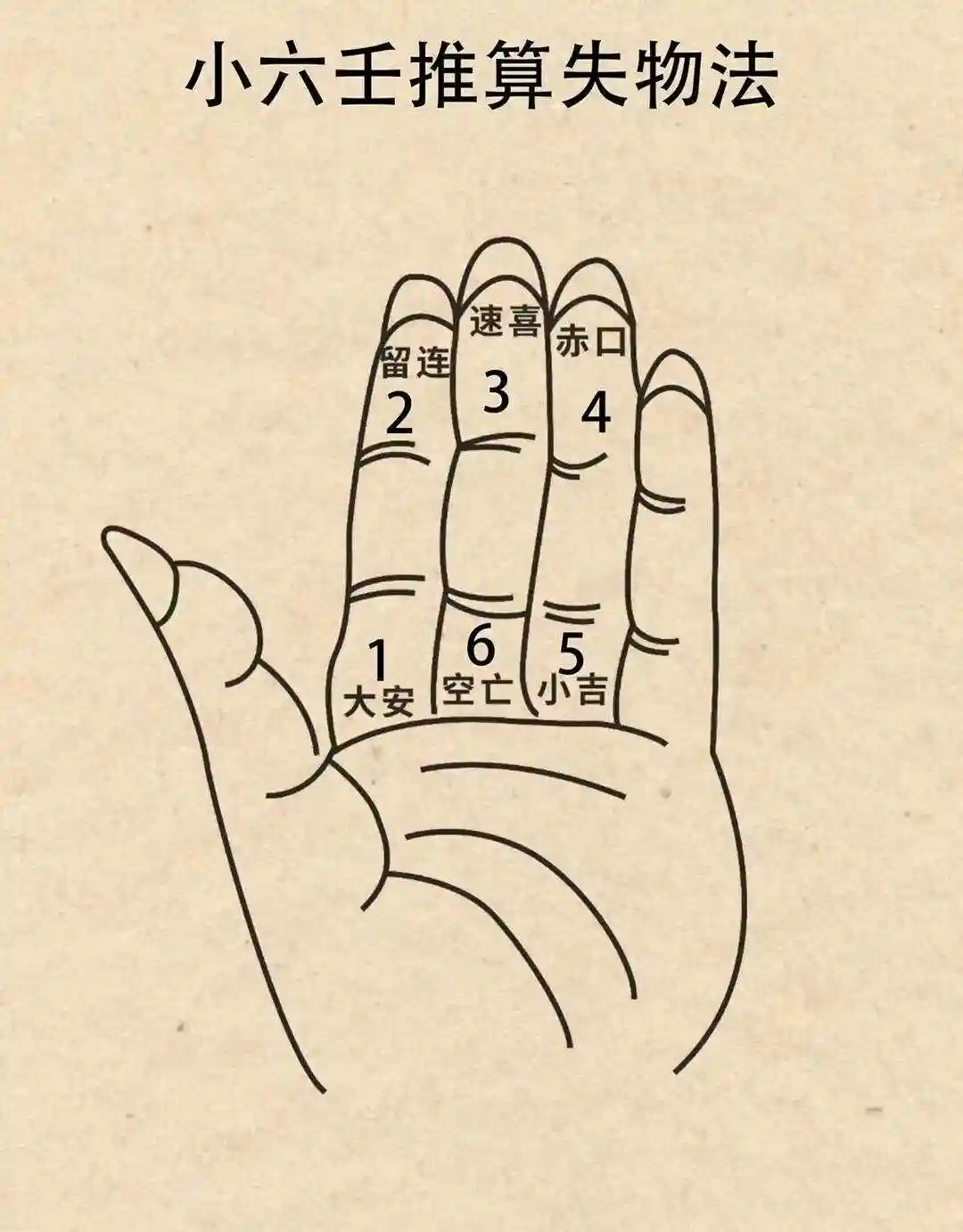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