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脑子里“嗡”地一声,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炸开了,炸得一片空白,只剩他最后那几个字,带着血沫的腥气,在里面撞来撞去。
血……沾了他的血……它们认我……
什么意思?
我呆滞地低下头,看自己的手。上面黑红一片,有干涸的,有新鲜的,混着泥土沙砾,黏腻地扒在皮肤上,指缝里都是。刚才拖他进门时蹭上的,给他擦嘴角时碰到的,摔在地上时沾的……全是他的血。
膝盖上,衣襟上,脚踝上……到处都是。
认我?
因为我碰了他的血?因为那些东西……闻到了?还是因为别的?因为……更早之前……
供桌上的烛火猛地爆开一个灯花,“啪”地一声脆响,在这死寂的观里显得格外刺耳。火光跟着剧烈摇晃了几下,墙上的影子张牙舞爪地扭曲了一瞬。
几乎是同时,门外传来了声音。
不是笑声,也不是脚步声。
是抓挠的声音。
很轻,很密,开始像是细小的爪子试探地刮擦着老旧的门板,发出“刺啦……刺啦……”的轻响。渐渐地,那声音越来越响,越来越急,从一处蔓延到整扇门板,上下左右,无处不在。不像是指甲,倒像是……很多很多细密的、坚硬的东西,同时刮在木头上。
“吱嘎——吱嘎——”
门板在轻微地颤动。尘土从门框上方簌簌落下。
它们来了。就在门外。贴着门板。
我浑身的汗毛一根根倒竖起来,心脏缩成一团,几乎停止跳动。眼睛死死瞪着那两扇不断震颤、发出不堪重负呻吟的木门。门闩只是一根不算粗的木棍,插在门环里,此刻正随着抓挠的节奏,一下,一下,轻微地跳动。
会撑不住的。
这个念头清晰无比地砸进我混沌的脑海。
我猛地扭头,看向地上无声无息的他,又看向四周。空荡荡的道观,除了神像、供桌、蒲团,什么都没有。角落里堆着些杂物,我连滚带爬地冲过去,胡乱翻找。断裂的桌腿?不行,太短。破旧的香炉?太轻。都是没用的东西!
抓挠声越来越密集,几乎连成一片令人牙酸的噪音。门板的震颤加剧,门闩跳动的幅度越来越大,木头发出的呻吟声也越来越响,仿佛下一刻就要断裂。
怎么办?怎么办?!
目光扫过供桌,落在那个陶罐上。我扑过去,一把抱起陶罐,里面还剩小半罐水。水……有什么用?!
我的视线又落回他身上。血……他的血……
一个极其荒谬、带着血腥气的念头,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。他说,它们认他的血……如果……
我颤抖着手,扯下自己里衣还算干净的一角布料,冲到地上他身边。看着那身浸透血污的道袍,我咬了咬牙,闭着眼,将布料用力按在他腰间一处颜色最深、几乎成了黑色的血渍上。布料迅速吸饱了暗红黏腻的液体。
抓起那块湿漉漉、沉甸甸的布,我冲到门边。门板已经被撞得“砰砰”作响,不再是抓挠,是实实在在的撞击!门框周围的土墙都在簌簌掉渣,那根门闩眼看着就要从门环里蹦出来。
来不及多想,我踮起脚,抖开那块浸血的布,胡乱地、用力地涂抹在门板中间,从上到下,涂出一道歪歪扭扭、湿淋淋的暗红色痕迹。浓重的血腥味瞬间在门前弥漫开来,盖过了观里原本的香烛味。
就在布片贴上木门的刹那——
“砰!!!”
一声巨响,外面撞击的力道猛地增强了数倍,整个门框都剧烈一震,灰尘漫天。但紧接着,那持续不断的、狂暴的撞击声,停了。
抓挠声也停了。
死一样的寂静再次降临。
只有门板上,那道湿漉漉的血痕,在烛光下泛着诡异的暗光,血珠正顺着木头的纹理,缓慢地往下淌,拉出几条细长的、触目惊的红线。
我靠着门板滑坐下来,手里的布掉在地上,双臂控制不住地剧烈发抖。有用?那血……真的挡住了外面的东西?
这念头刚升起,还没来得及喘口气,观里的温度,毫无征兆地开始急剧下降。
不是寻常的夜寒,而是一种阴冷的、贴着骨头缝钻的寒意,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。供桌上的烛火猛地一矮,火苗缩成了可怜巴巴的一点豆大,颜色也变得幽绿幽绿,把整个道观映照得鬼气森森。
墙角,屋檐,神像背后……那些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里,开始浮现出淡淡的、灰白色的影子。不是实体,像雾,又像烟,扭动着,凝聚着,缓缓向观内弥漫。空气变得粘稠,每一次呼吸都像吸进了冰碴子,带着陈年灰尘和香灰的味道,还有……一丝极淡、却无法忽视的檀香。
这不是从门外来的。
这东西,一直在观里。
我惊恐地环顾四周,那些灰白的雾气越来越浓,渐渐能看出模糊的、不成形的人影轮廓,无声地摇曳着,朝着中心——我和他躺倒的地方——聚拢过来。烛火绿莹莹的光照在它们身上,却穿透过去,照出后面更加浓重的黑暗。
冷,刺骨的冷。不是身体的冷,是心里头透出来的,绝望的冷。
我连滚带爬地退回他身边,徒劳地想把他挡在身后,虽然我自己也抖得像筛糠。眼睛慌乱地扫视,最后定格在他腰间——那里,除了血迹,似乎还挂着一个什么东西,之前被血污盖住了没看清。
是一个小小的、深紫色的旧布袋,用同色的细绳系着,绳头都磨得起了毛边。布袋只有半个巴掌大,瘪瘪的,看不出里面装着什么。
几乎是一种本能,我伸手就去扯那个布袋。手指触到布袋的瞬间,一股极其微弱的暖意,顺着指尖传来,虽然微弱,却和观里无处不在的阴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与此同时,周围那些逼近的灰白影子,似乎齐齐顿了一下。
有用?
我心脏狂跳,用力一拽,把系绳扯断,将布袋抓在手里。触手粗糙,里面似乎装着一些硬硬的小颗粒,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、质地特别的纸。
我哆哆嗦嗦地打开布袋,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掌心。
是几粒干瘪发黑的、像是植物种子又像是什么矿石的东西,认不出。还有一张折叠成三角状的、暗黄色的纸符。纸符很旧了,边缘磨损,但上面的朱砂符文却依旧鲜红刺眼,笔画虬结盘绕,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古朴威压。
就在我拿起那张三角符的瞬间——
“呼——”
观内凭空卷起一阵阴风,带着尖啸,直扑我面门!那些原本只是缓慢聚拢的灰白影子,像是被激怒了一般,骤然变得清晰、狂躁,张牙舞爪地扑了过来!绿色烛火疯狂摇曳,几乎熄灭!
避无可避!
我吓得魂飞魄散,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,闭着眼,将手里那张三角符,朝着阴风最盛、影子最浓的方向,用力扔了出去!
没有金光大作,也没有雷霆震响。
只有极其轻微的一声,像是火星掉进冰水里,“嗤”地一下。
扑到眼前的阴风,散了。
狂舞的灰白影子,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拍散,发出一片无声的、凄厉的尖啸,瞬间退回了角落的黑暗里,变得淡薄,然后消失不见。
观内重新安静下来。只有那点豆大的、幽绿色的烛火,勉强跳动着,将熄灭未熄。
我瘫软在地,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空瘪的旧布袋,掌心被里面残留的硬粒硌得生疼。刚才那一瞬的暴烈对抗,仿佛耗尽了观内某种支撑的力量。烛火越来越暗,绿光惨淡,只能照亮咫尺之地。门板上的血痕,在幽暗光线下,更像一道干涸的、不祥的伤口。
我看向地上依旧昏迷的他,又看看自己满身的血污,和手里这张似乎耗尽力量、颜色都黯淡了些的旧符。
挡住了?暂时挡住了?
可接下来呢?血会干,符……这符还能用几次?蜡烛眼看就要灭了。等烛火一熄,这观里,门外……
我挪到他身边,借着最后一点微光,看他惨白的脸。他眉心那点暗沉的颜色,似乎又扩散了一点点,像一滴墨,慢慢在清水里洇开。
外面,死寂重新笼罩。但我知道,那抓挠声,那笑声,那浓得化不开的黑暗,还有观里这些不知何时又会凝聚的鬼影子……它们都在等着。
等着烛灭。
等着我们……油尽灯枯。
一种比之前任何恐惧都要深沉的疲惫和绝望,沉沉地压了下来。我握紧了手里微温的布袋和那张冰冷的旧符,目光在昏暗中,落向他紧闭的唇,和唇边干涸的血迹。
沾了他的血……它们认我……
那如果……不止是血呢?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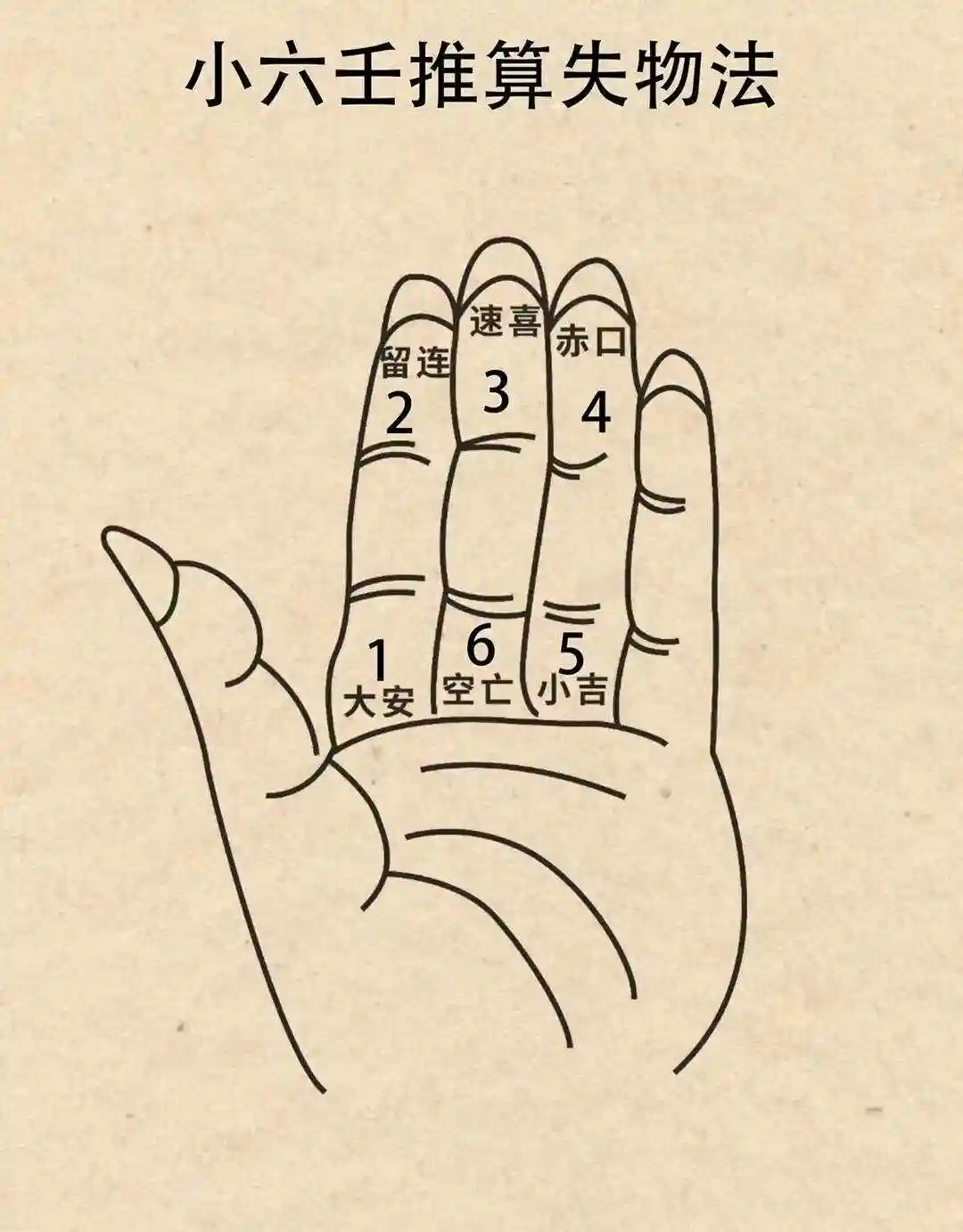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