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道门规矩,不可近色。”
他总这样对我说,却在我病重时破了戒。
“只此一次,为救你性命。”
事后他面色苍白,转身就走。
而我身上开始发生怪事——总闻到若有若无的檀香味,夜晚总有脚步声在窗外徘徊。
直到那晚,我看见他满身是血站在我床前:
“它来了,跟我走。”
灶上熬的药咕嘟咕嘟响,那股子苦味浸透了老屋的每一条缝。我裹着厚被子,还是冷,骨头缝里都往外冒寒气。窗外天阴得厉害,怕是又要落雪。这病拖了有小半个月了,吃了多少帖药都不见好,人虚得下不了床,脑子里昏昏沉沉,有时都觉得魂儿要飘出去。
门轴“吱呀”一声轻响,一股清冽的、带着外面寒气的风先钻了进来。他没敲门,向来如此。玄青色的道袍下摆有些湿,沾了泥点子,鞋上也是。他没看我,径直走到灶边,掀开药罐盖子看了看,又拿起一旁的蒲扇,不紧不慢地扇着炉火。侧脸在明明灭灭的火光里,没什么表情,像后院那尊很久没人打理的石像。
屋子里只有药沸的声音和我压抑的咳嗽。
“道长……”我哑着嗓子叫他。
他动作没停:“药还须一刻。”
我知道他不爱说话,尤其不爱搭理我这些在他看来无关紧要的招呼。他是这偏远山村里唯一的道士,住在村尾更破旧的道观里,平时给村人画个符、治个头疼脑热,也主持红白事,话少,本事据说有些,但也孤僻得很。我这次病得蹊跷,郎中都摇头,家里人没法子,半请半逼地把他求了来。他来看过两次,每次都皱着眉,说“阴气缠身,药石罔效”,然后留下些画了奇怪符号的黄纸让我烧了喝,或者贴在门窗上。有点用,但压不住根。
“我是不是……好不了了?”这话带着我自己都没察觉的颤音。太难受了,那种一点点被掏空、被冻僵的感觉。
他扇火的动作顿了一下,终于转过脸,目光落在我身上。那眼神很深,像井水,看不出情绪,但被他看着,那股没着没落的恐慌奇异地平息了一点。“死不了。”他声音平平,“别瞎想。”
可那天夜里,我突然就不行了。不是咳嗽,也不是发冷,是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压住,一口气怎么也吸不上来,手脚冰冷发麻,耳朵里嗡嗡响,眼前的房梁都在晃,模糊听见娘在旁边哭喊。我知道,这回可能真的到头了。意识像风里的蜡烛,忽明忽暗。
混乱中,有人拨开我娘,靠得很近。熟悉的、淡淡的香火味,混着一种凛冽的、像雪后松针的气息。是那个道士。
“……元阳已散,阴煞入心……”断断续续的字眼飘进我耳朵,像是隔着一层水。他的声音比平时更沉,更紧,“……寻常法子……来不及了……”
然后,我感觉到滚烫的掌心贴上了我的额头,那温度极高,烫得我一哆嗦,却奇异地把我正在涣散的神魂钉住了一点。紧接着,更炽热的气息覆了上来,不是额头,是……嘴唇。干燥的,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、类似铁锈又似檀香的味道,强硬地撬开我的牙关,一股灼热的气流直冲进来,瞬间涌向四肢百骸!
我震惊得忘了挣扎,或者说,根本无力挣扎。模糊的视线里,是他放大的、紧闭的双眼,和微微颤动的、沾了不知是汗还是别的什么的睫毛。道袍的领口蹭着我的下巴,粗糙的布料摩擦着皮肤。
时间好像静止了。那渡过来的气息起初像火,烧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,随即又化作温润的暖流,一遍遍冲刷着冰冷僵硬的经脉。压在心口那块巨石,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,慢慢松动、碎裂。不知过了多久,可能只是一瞬,也可能极其漫长,他猛地撤离,动作快得像被火烫到。
我瘫软在床,大口喘着气,胸膛剧烈起伏,久违的空气涌入肺腑,带着活过来的刺痛。而他,踉跄着退开两步,背过身去。我看不见他的脸,只看到他撑在旧桌沿上的手,指节用力到发白,玄青色的道袍后背,竟在油灯昏暗的光下,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,像是……汗透的。
“只此一次。”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,每个字都像是从石头缝里挤出来的,“为救你性命。道门……规矩不可近色。你……好自为之。”
说完,他没再看我,也没理会我娘带着哭腔的追问和道谢,拉开门,身影迅速没入外面浓稠的夜色里,脚步似乎有些虚浮。
我活过来了。第二天就能勉强喝下粥,不到三天,竟能下地走动了。村里人都说是道长用了秘法,救了条命。娘去道观送谢礼,回来说道长闭门不见,脸色似乎不太好。
身体是好得利索了,可有些东西,不对劲了。
我开始总闻到一股檀香味。不是道观里那种浓烈持久的香火味,是极淡的,丝丝缕缕的,冷不丁就钻进鼻子。有时在吃饭,有时在晒太阳,有时半夜醒来,那味道就在枕边,清冷干净,却挥之不去。我起初以为是病久了嗅觉出了问题,或者沾染了他袍子上的味道,可换了被褥、洗澡、熏艾草,都没用。那味道像认准了我,如影随形。
更让我心里发毛的是晚上的动静。老屋的窗户是纸糊的,夜深人静时,外面一点声响都听得真切。起初是觉得院里有脚步声,很轻,沙沙的,像踩着落叶。我以为是野猫或者黄鼠狼,没在意。可后来,那脚步声越来越清晰,就停在窗外,不动了。好像有什么东西,隔着一层薄薄的窗纸,静静地站在那里,朝里望。我能感觉到“它”的注视,冰冷,黏腻,带着说不清的恶意。我不敢动,浑身僵硬地躺着,直到鸡叫头遍,那脚步声才又沙沙地远去。
我跟娘提过两次,她摸摸我的头,说是病刚好,神魂不稳,容易惊悸,让我别多想。可我知道不是。那感觉太真实了。而且,我发现我床头贴着的、他之前给的黄符,边角不知何时微微卷了起来,颜色也暗淡了些。
恐惧像蔓草,悄悄滋生,缠绕心脏。我开始害怕天黑,害怕独处,害怕那随时可能出现的檀香味和窗外的脚步。我变得疑神疑鬼,总觉得暗处有眼睛。我想去找他,那个道士,可想起他那夜决绝离去的背影和“好自为之”的话,脚又像钉在地上。
直到那个晚上。
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住,一丝光也没有。风刮得厉害,窗户纸呼啦呼啦响。我缩在被子里,睁着眼睛,毫无睡意。檀香味比任何一晚都浓,浓得我有些窒息。窗外的脚步声又来了,不似往常的徘徊,而是径直走到窗前,停下。
然后,我听到了极其轻微的“刺啦”一声,像是……指甲刮过窗纸。
我头皮猛地炸开,血液瞬间冲向头顶,又冻成冰碴子。我死死咬住被子,不敢发出一点声音,眼睛惊恐地瞪着窗户的方向。
一片死寂。
就在我几乎要崩溃的时候,房门方向,传来“砰”的一声闷响!不是风,是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撞在了门上。
紧接着,门闩从外面被大力撞断,木屑飞溅!房门洞开,一个黑影挟裹着浓重得令人作呕的血腥气,跌撞进来。
是那个道士!
油灯早灭了,只有窗外透进极其微弱的天光,勾勒出他一个模糊骇人的轮廓。玄青色的道袍几乎看不出本色,浸透了深色的、黏腻的液体,紧紧贴在身上。他脸上、手上也都是血,有些已经发黑凝固,有些还在顺着指尖往下滴落,在冰冷的地面上溅开一小朵一小朵暗色的花。他脸色惨白如纸,嘴唇却是一种诡异的青紫色,胸口剧烈起伏,喘着粗气,仿佛刚经历了一场殊死搏杀。唯有那双眼睛,在黑暗中亮得吓人,死死地、精准地盯住了床上的我。
浓烈的血腥味瞬间盖过了檀香,充斥着整个房间。
他朝我伸出手,那只沾满血的手,颤抖着,却异常坚定。
“它来了。”他的声音嘶哑破碎,气若游丝,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绝望和急迫,“跟我走……快!”
我僵在床上,看着他身后洞开的、仿佛要吞噬一切的房门黑暗,以及他身上那触目惊心的血,浑身的血液都凉透了。
跟我走……走去哪里?外面……有什么?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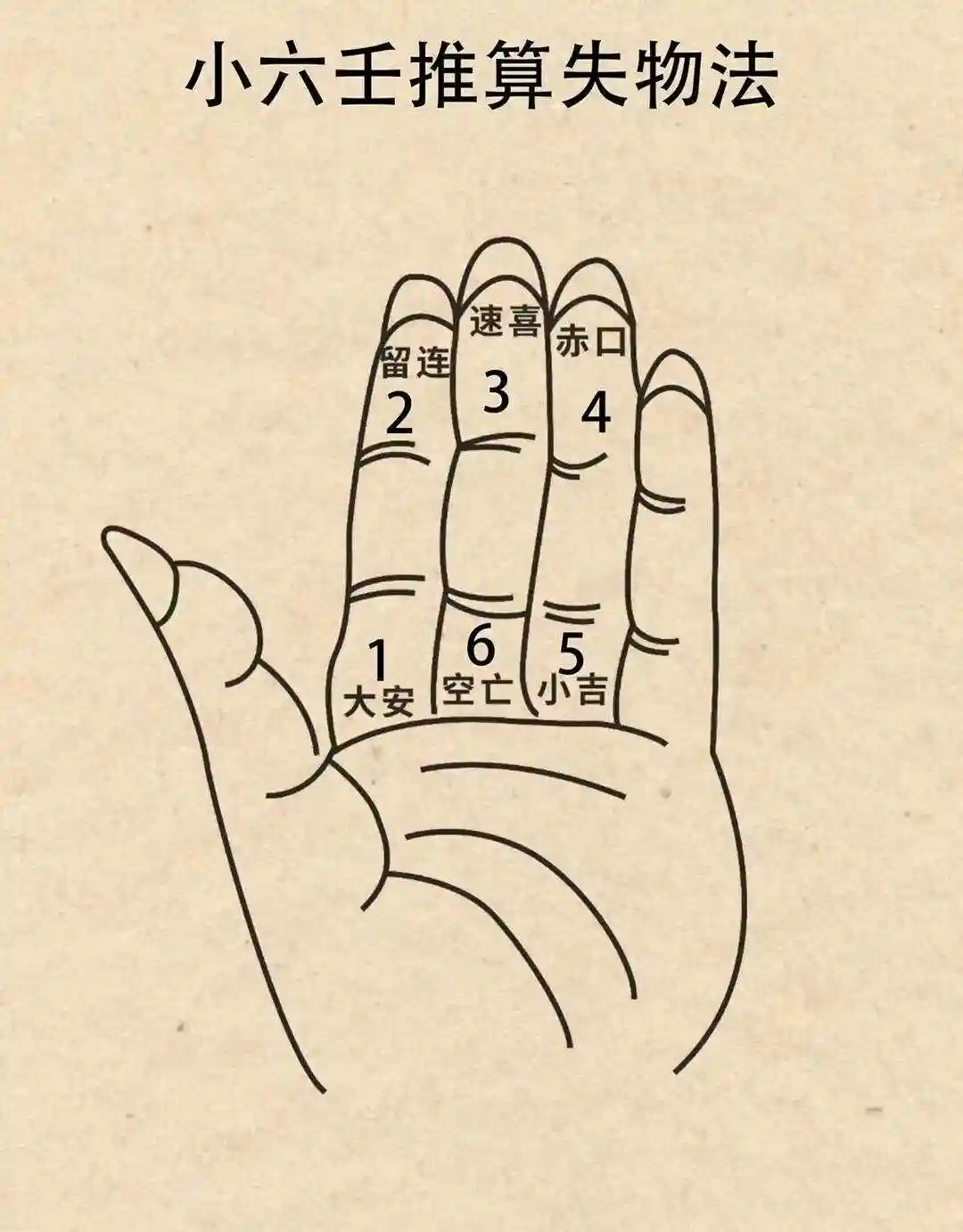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