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张着嘴,喉咙里像塞了团棉花,一个音都发不出来。眼睛瞪得老大,只看得见他伸过来的那只手——手指修长,本该是画符持剑的手,此刻糊满了暗红黏腻的血,指甲缝里都是黑的,血珠沿着指尖颤巍巍悬着,要滴不滴。
时间好像被他身上的血腥味冻住了。
“走……啊!”他又低吼了一声,那声音像破风箱里扯出来的,带着铁锈的腥气。他往前踉跄半步,差点栽倒,全靠另一只手死死撑住门框,指节抠得发白。门框上的旧木屑簌簌往下掉,混进他袍子下摆滴落的血里。
这一下,像是猛地扯断了我脑子里那根僵住的弦。我根本来不及想,手脚并用,几乎是滚下床的。被子缠在腿上,冰凉的砖地激得我一哆嗦。我胡乱踢开被子,赤着脚就朝他扑过去——不敢碰他,只敢挨着他袖角一点没被血浸透的布料。
他见我动了,猛地转身,力道大得带起一阵腥风。那件浸饱了血的道袍下摆扫过我的脚背,湿冷黏腻的触感让我胃里一阵翻腾。
门外是浓得化不开的黑。没有月亮,没有星星,连远处村舍本该零星的光点也全都熄灭了。只有风,鬼哭一样号着,卷着地上的沙石枯叶,打在脸上生疼。空气里除了血腥,还有一股……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很久的甜腥气,混在风里,无孔不入。
他走得极快,步子又大又急,但身形不稳,深一脚浅一脚,踩在碎石路上发出“嘎吱”的闷响,混着他压抑的、粗重的喘息。我跌跌撞撞跟在他后面,赤脚踩过冰冷粗糙的地面,被碎石硌得生疼,却不敢慢一步。眼睛紧紧盯着他那片在黑暗中移动的、湿漉漉的玄青色背影,那是唯一能抓住的浮木。
我们没走大路,直接扎进了村后那片老林子。枝叶遮天,进了林子,那点子微弱的天光也没了,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只能听见风摇树影的哗啦声,还有我们两人仓促凌乱的脚步和喘息。
我什么都看不见,全凭感觉跟着他。好几次差点被突出的树根绊倒,膝盖磕在硬土上,火辣辣地疼。他却像能夜视,左拐右绕,没有半分迟疑。只是他身上的血,滴落的频率越来越高,在身后留下断续的、甜腥的痕迹。
忽然,他猛地停下。我猝不及防,一头撞上他后背。那湿冷的、带着浓重铁锈味的触感让我惊叫一声,又死死捂住嘴。
他侧耳听着什么,身体绷得像拉满的弓。我也屏住呼吸,竖起耳朵。
除了风声,林子深处,好像……多了点别的。
很轻,很碎,像是很多双脚在厚厚的落叶上拖沓着走,又像是很多张嘴在极近的地方,贴着耳朵呼气,嘶嘶的,带着湿冷的气流。不是从一个方向来,是从四面八方,慢慢围拢。
檀香味。那股阴魂不散的檀香味,又出现了。这一次,浓得令人作呕,死死压在那腐烂的甜腥气之上,像一张湿透的厚毯子,蒙住口鼻。
他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,发出一声极低的、近乎呜咽的抽气。然后,他抓住我的手腕——那只血手,冰冷,黏滑,力气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——不由分说,拖着我朝林子更深处狂奔!
“不能停……不能回头……”他嘶哑的声音破碎在风里,更像是一句诅咒。
我们像两只被猎犬追赶的兔子,在林间亡命奔逃。树枝抽打在脸上、身上,留下火辣辣的疼。肺里像着了火,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味。身后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,那拖沓的脚步声,那嘶嘶的呼气声,越来越近,越来越密,仿佛就在颈后。
直到眼前出现了一点微弱的光。
是那间破旧的道观。歪斜的门扉透出一点晕黄,在这无边的漆黑里,脆弱得像风中的残烛。
他速度更快了,几乎是把我甩向那扇门。我扑到门前,手忙脚乱地去推。门没闩,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温暖的烛光涌出来,晃得我眼睛一花。
我刚要迈进去,身后猛地传来一声压抑的闷哼,紧接着是重物倒地的声音。
我骇然回头。
他就倒在门槛外三步远的地方,脸朝下,一动不动。玄青色的道袍铺开,像一片被污血浸透的、巨大的叶子。血从他身下汩汩漫开,沿着石阶的缝隙,缓慢地、执着地,流向道观的门槛。
而那一片令人窒息的漆黑里,拖沓的脚步声,嘶嘶的呼气声,还有那浓郁到实质般的檀香,已经逼到了林子边缘,就在那片空地的对面,蠢蠢欲动。
门槛里是晕黄的、看起来安全的光。门槛外是他倒在血泊里无声无息的身体,和即将扑上来的、未知的恐怖。
我站在光与暗的交界处,一只脚在里,一只脚在外,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。
进去?把门关上?
还是……把他拖进来?
 添加师父微信
添加师父微信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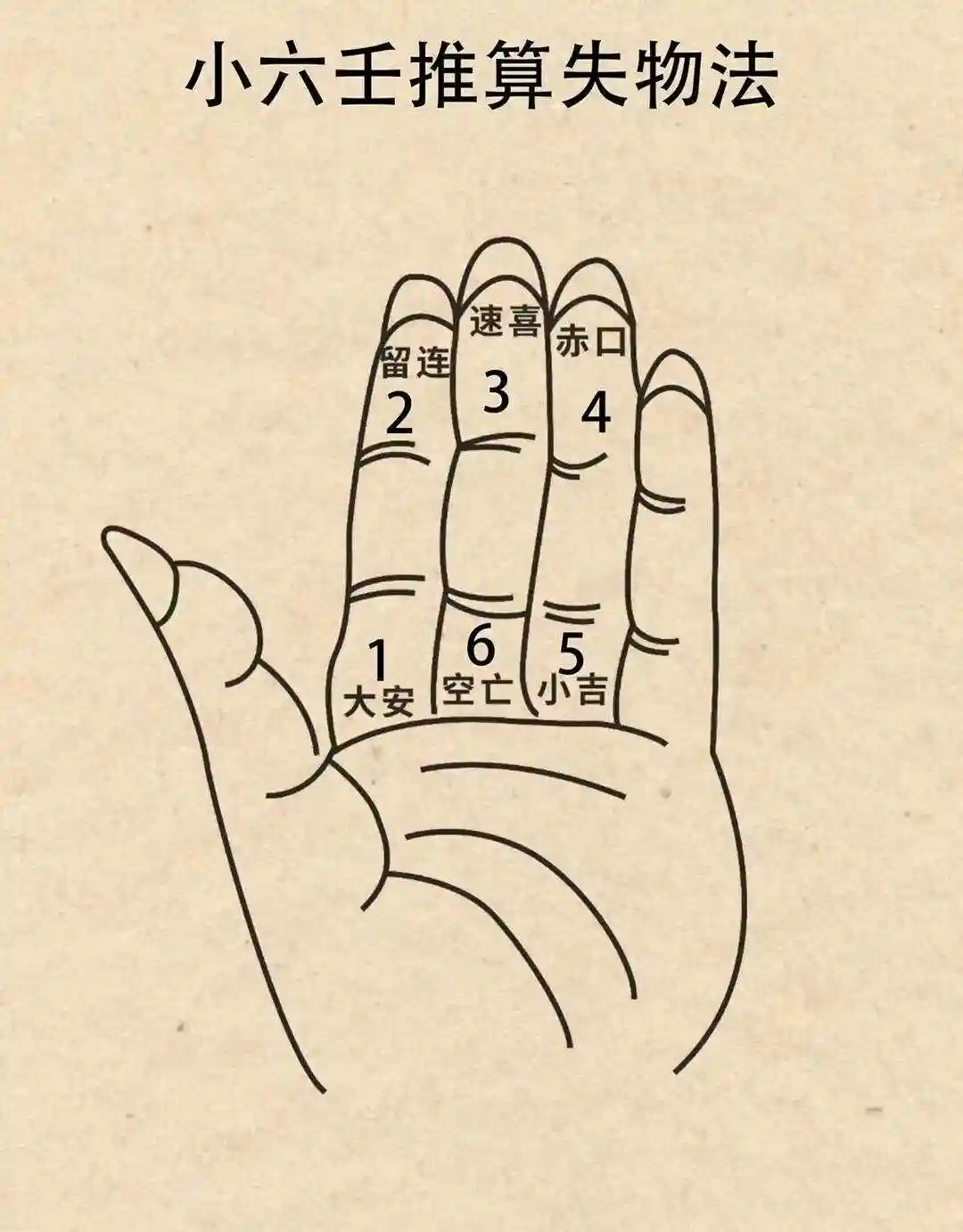


发表评论